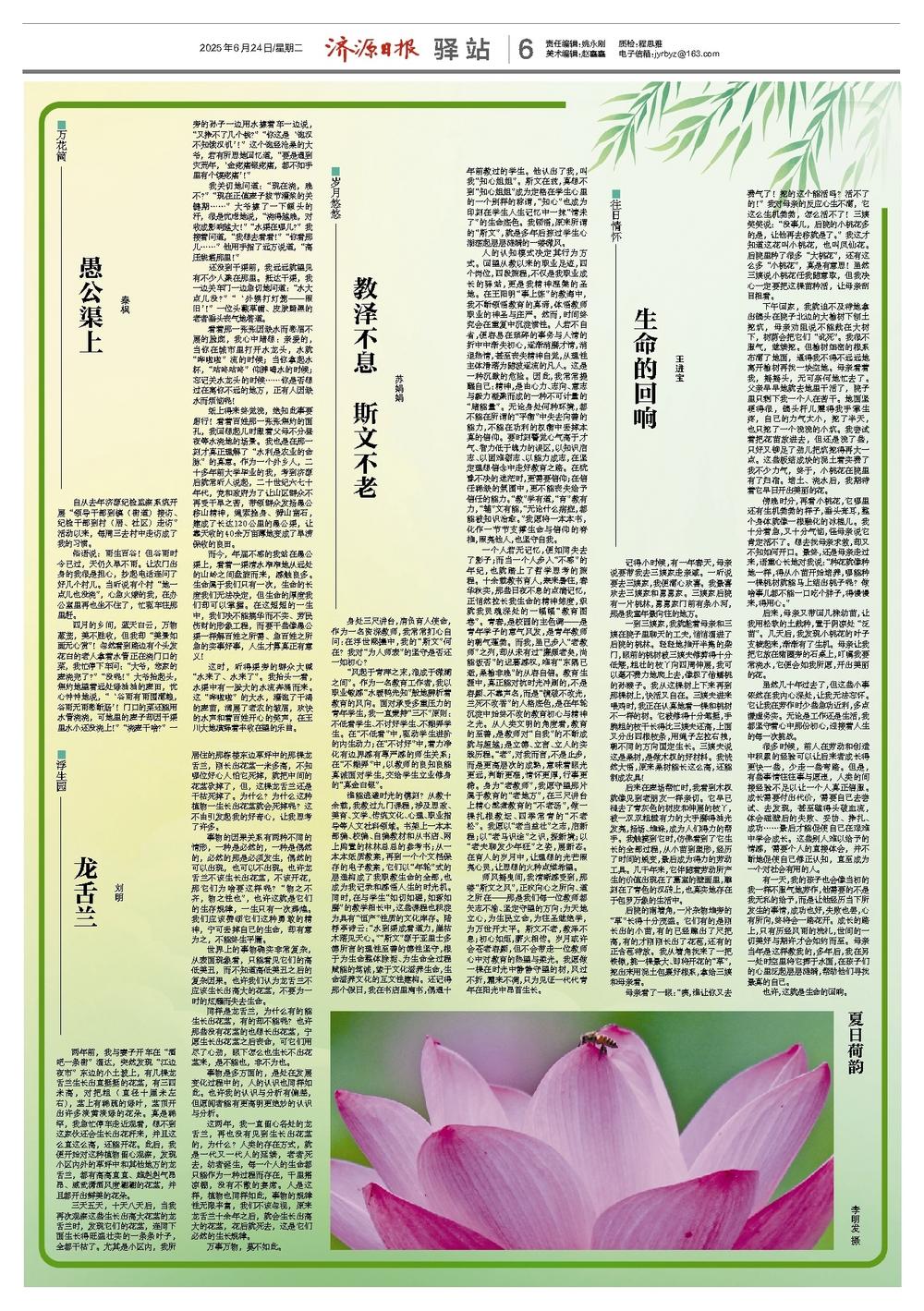记得小时候,有一年春天,母亲说要带我去三姨家走亲戚。一听说要去三姨家,我便满心欢喜。我最喜欢去三姨家和舅舅家。三姨家后院有一片桃林,舅舅家门前有条小河,那是我童年最向往的地方。
一到三姨家,我就趁着母亲和三姨在院子里聊天的工夫,悄悄溜进了后院的桃林。轻轻地推开半掩的柴门,眼前的桃树被三姨夫修剪得十分低矮,粗壮的枝丫向四周伸展,我可以毫不费力地爬上去,像极了偷蟠桃的孙猴子。我从这棵树上下来再到那棵树上,快活又自在。三姨夫进来喂鸡时,我正在认真地看一棵和桃树不一样的树。它被修得十分笔挺,手腕粗的枝干长得比三姨夫还高,上面又分出四根枝条,用绳子左拉右拽,朝不同的方向固定生长。三姨夫说这是桑树,是做木杈的好材料。我恍然大悟,原来桑树能长这么高,还能制成农具!
后来在麦场帮忙时,我看到木杈就像见到老朋友一样亲切。它早已褪去了青灰色的树皮和伸展的枝丫,被一双双粗糙有力的大手磨得油光发亮,扬场、堆垛,成为人们得力的帮手。我触摸到它时,仿佛看到了它生长的全部过程,从小苗到塑形,经历了时间的蜕变,最后成为得力的劳动工具。几千年来,它伴随着劳动所产生的价值出现在了墓室的壁画里,雕刻在了青色的汉砖上,也真实地存在于包罗万象的生活中。
后院的南墙角,一片杂物堆旁的“草”长得十分茂盛。它们有的是刚长出的小苗,有的已经蹿出了尺把高,有的才刚刚长出了花苞,还有的正含苞待放。我从墙角找来了一把铁锹,挑一棵最大、即将开花的“草”,挖出来用泥土包裹好根系,拿给三姨和母亲看。
母亲看了一眼:“咦,谁让你又去费气了!挖的这个能活吗?活不了的!”我对母亲的反应心生不满,它这么生机勃勃,怎么活不了!三姨笑笑说:“没事儿,后院的小桃花多的是,让他再去移就是了。”我这才知道这花叫小桃花,也叫凤仙花。后院里种了很多“大桃花”,还有这么多“小桃花”,真是有意思!虽然三姨说小桃花任我随意取,但我决心一定要把这棵苗种活,让母亲刮目相看。
下午回家,我就迫不及待地拿出镐头在院子北边的大榆树下刨土挖坑,母亲劝阻说不能栽在大树下,树荫会把它们“讹死”。我很不服气,继续挖。但榆树细密的根系布满了地面,逼得我不得不远远地离开榆树再找一块空地。母亲看着我,摇摇头,无可奈何地忙去了。父亲早早地就去地里干活了,院子里只剩下我一个人在苦干。地面坚硬得很,镐头杆儿震得我手掌生疼,自己的力气太小,挖了半天,也只挖了一个浅浅的小坑。我尝试着把花苗放进去,但还是浅了些,只好又铆足了劲儿把坑挖得再大一点。这些板结成块的泥土着实费了我不少力气,终于,小桃花在院里有了归宿。培土、浇水后,我期待着它早日开出美丽的花。
傍晚时分,再看小桃花,它哪里还有生机勃勃的样子,垂头耷耳,整个身体就像一根融化的冰棍儿。我十分着急,又十分气恼,怪母亲说它肯定活不了。想去找母亲求救,却又不知如何开口。最终,还是母亲走过来,语重心长地对我说:“种花就像种地一样,得从小苗开始培养,哪能种一棵桃树就能马上结出桃子呢?做啥事儿都不能一口吃个胖子,得慢慢来,得用心。”
后来,母亲又带回几株幼苗,让我用松软的土栽种,置于阴凉处 “泛苗”。几天后,我发现小桃花的叶子支棱起来,渐渐有了生机。母亲让我把它放在猪圈旁的石桌上,叮嘱我要常浇水,它便会如我所愿,开出美丽的花。
虽然几十年过去了,但这些小事依然在我内心深处,让我无法忘怀。它让我在劳作时少些急功近利,多点谦虚务实。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我都坚守着心中那份初心,迎接着人生的每一次挑战。
很多时候,前人在劳动和创造中积累的经验可以让后来者成长得更快一些,少走一些弯路。但是,有些事情往往事与愿违,人类的间接经验不足以让一个人真正信服。成长需要付出代价,需要自己去尝试、去发现,甚至磕得头破血流,体会碰壁后的失败、妥协、挣扎、成功……最后才能促使自己在艰难中学会成长。这些别人难以给予的情感,需要个人的直接体会,并不断地促使自己修正认知,直至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有一天,我的孩子也会像当初的我一样不服气地劳作,他需要的不是我无私的给予,而是让他经历当下所发生的事情,成功也好,失败也罢,心有所向,终将会一路花开。成长的路上,只有历经风雨的洗礼,世间的一切美好与期许才会如约而至。母亲当年是这样教我的,多年后,我在另一处时空里将它掷于水面,在孩子们的心里泛起层层涟漪,帮助他们寻找最真的自己。
也许,这就是生命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