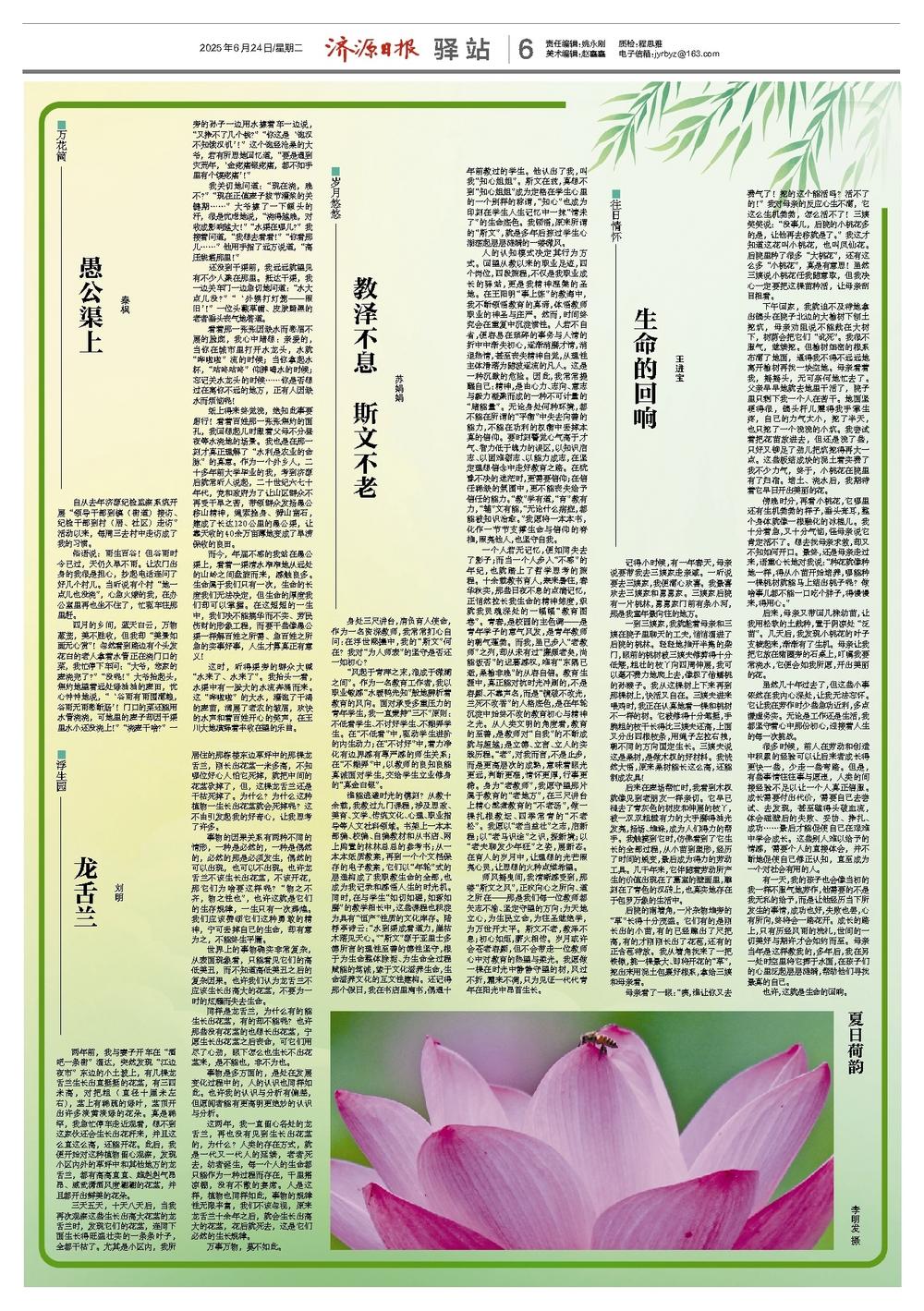身处三尺讲台,肩负育人使命,作为一名资深教师,我常常扪心自问:在浮世熙攘中,我的“斯文”何在?我对“为人师表”的坚守是否还一如初心?
“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以职业敏感“水暖鸭先知”般地辨析着教育的风向。面对承受多重压力的青年学生,我一直秉持“三不”原则:不低看学生、不讨好学生、不糊弄学生。在“不低看”中,驱动学生进阶的内生动力;在“不讨好”中,着力净化有边界感有尊严感的师生关系;在“不糊弄”中,以教师的良知良能真诚面对学生,交给学生立业修身的“真金白银”。
谁能逃避时光的镌刻?从教十余载,我教过九门课程,涉及思政、美育、文学、传统文化、心理、职业指导等人文社科领域。书架上一本本部编、校编、自编教材和从书店、网上购置的林林总总的参考书;从一本本纸质教案,再到一个个文档保存的电子教案,它们以“年轮”式的层递构成了我职教生命的全部,也成为我记录和感悟人生的时光机。同时,在与学生“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教学相长中,这些课程也积淀为具有“恒产”性质的文化库存。陆桴亭诗云:“水到渠成看道力,崖枯木落见天心。”“斯文”源于亚里士多德所言的理性至善的德性坚守,根于为生命整体除垢、为生命全过程赋能的笃诚,缘于文化滋养生命,生命滋养文化的互文性建构。还记得那个假日,我在书店里淘书,偶遇十年前教过的学生。他认出了我,叫我“知心姐姐”。斯文在兹,真想不到“知心姐姐”成为定格在学生心里的一个别样的称谓,“知心”也成为印刻在学生人生记忆中一抹“情未了”的生命底色。我顿悟,原来所谓的“斯文”,就是多年后掠过学生心湖荡起层层涟漪的一缕微风。
人的认知模式决定其行为方式。回望从教以来的职业足迹,四个岗位,四段旅程,不仅是我职业成长的驿站,更是我精神涅槃的圣地。在王阳明“事上练”的教诲中,我不断领悟教育的真谛,体悟教师职业的神圣与庄严。然而,时间终究会在重复中沉淀惯性。人若不自省,便容易在琐碎的事务与人情的折中中渐失初心,逐渐消磨才情,消退热情,甚至丧失精神自觉,从理性主体滑落为随波逐流的凡人。这是一种沉默的危险。因此,我常常提醒自己:精神,是由心力、志向、意志与毅力凝聚而成的一种不可计量的“暗能量”。无论身处何种环境,都不能在所谓的“平衡”中失去向善的能力,不能在功利的权衡中丢掉本真的信仰。要时刻警觉心气高于才气、智力低于魄力的误区,以知识启志、以困难砺志、以能力成志,在坚定理想信念中走好教育之路。在犹豫不决的迷茫时,更需要信仰;在信任稀缺的氛围中,更不能丧失给予信任的能力。“教”学有道,“育”教有力,“辅”文有能,“无论什么病症,都能被知识治愈。”我愿将一本本书,化作一节节支撑生命与信仰的脊椎,照亮他人,也坚守自我。
一个人若无记忆,便如同失去了影子;而当一个人步入“不惑”的年纪,也就踏上了哲学思考的旅程。十余载教书育人,寒来暑往,春华秋实,那些日夜不息的点滴记忆,正悄然拉长我生命的精神纬度,织就我灵魂深处的一幅幅“教育图卷”。青春,是校园的主色调——是青年学子的意气风发,是青年教师的朝气蓬勃。而我,虽已步入“老教师”之列,却从未有过“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迟暮感叹,唯有“东隅已逝,桑榆非晚”的从容自信。教育生涯中,真正能对抗时光冲刷的,不是容颜、不靠声名,而是“镜破不改光,兰死不改香”的人格底色,是在年轮沉淀中始终不改的教育初心与精神之光。从人类文明的角度看,教育的至善,是教师对“自我”的不断成就与超越;是立德、立言、立人的实践历程。“老”,对我而言,不是止步,而是更高层次的成熟,意味着眼光更远,判断更准,情怀更厚,行事更稳。身为“老教师”,我愿守望那片属于教育的“老地方”,在三尺讲台上精心熬煮教育的“不老汤”,做一棵扎根教坛、四季常青的“不老松”。我愿以“老当益壮”之志,启新程;以“老马识途”之识,探新境;以“老夫聊发少年狂”之姿,展新态。在育人的岁月中,让理想的光芒照亮心灵,让思想的火种点燃希望。
师风摇曳间,我清晰感受到,那缕“斯文之风”,正吹向心之所向、道之所在——那是我们每一位教师都矢志不渝、坚定守望的方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斯文不老,教泽不息;初心如炬,薪火相传。岁月或许会苍老容颜,但不会带走一位教师心中对教育的热望与柔光。我愿做一棵在时光中静静守望的树,风过不折,霜来不凋,只为见证一代代青年在阳光中昂首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