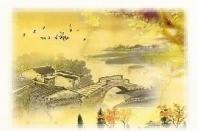眼看我们小弟兄三人都快长大了,姐也快成年人了,不能再蹿房檐住了,1963年,父亲决定勒紧腰带也要盖上三间瓦房。很快,房是建起来了,是那种简陋型的,屋顶的瓦是干摆上的,粉墙是黑泥巴伴麦秸,裱墙是土坯砌起来的。没有棚楼,是那种一眼可望见屋顶梁檩椽的。即便是这样,因为是自己的,父母有了些许安慰,脸上也常挂几分笑意。房是在老宅基地上重建的,常勾起父亲的回忆。他说老宅可漂亮了,青砖铺地,胡梯合缝木板楼,屋顶有脊兽,在村里是数得上的,只可惜一夜间被日本鬼子一把火给烧成了残垣断壁。新房没有棚楼,可利用空间缩小了一半,家什杂物摆放凌乱不堪,我们做梦都想上棚楼,哪怕是一间的。可是抖尽家底,也只有几块歪扭不整的木板。随着年龄的增长,父母已近老年,在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家庭收入没长多少,我们的力气却长了不少。力气也是做事的本钱。20世纪70年代初期,南山林场的洋槐林已进入成长鼎盛期,每到春末夏初,大批林业工人翻山越岭修剪槐林。大量的旁枝斜叉被剪除,这对于缺煤少柴的农家来说,无疑带来了利好。近水楼台先得月,一夜间,大量的村民涌向坡坡岭岭拾柴。他们攀爬于乱石荆棘丛中,常被槐刺挂破手指也在所不惜。后来不知是谁发现了洋槐嫩枝的附加值,选一些条形周正、粗细适中的枝条能用于土屋编楼。有了更高的利用价值,洋槐条一下子成了拾柴人的香饽饽,就连普通的修剪工人也有了自己的身价,从中搞起隐形特权,将自己修剪下来的好枝优先给予那些熟识的关系户。有时,一枝还没剪下来,却早在众目睽睽之中了,只待枝条落地那一刻,粥少僧多,不是捡而是抢了。为一己小利,我的原本友善的乡亲,常因拾柴闹出不和谐的尴尬。尽管如此,凭借我们几个强壮劳力的优势,门前的柴堆还是与日俱增,好条形修整得也愈来愈多。记得有一次,我和哥的运气特好,我们说那是发“洋财”了,其实就是每人拾了两大捆好槐条。因路途远、柴担重,加上林间无路,时有荆棘磕绊,只待星月出齐才下得山来。日子的艰辛,生活的磨难,让在家门口守望的母亲落下了牵挂的眼泪。材料有了,父亲正式向我们宣布要编一间洋槐楼。
编楼是个技术活,本家九爷聂乃祥有此手艺,受邀后欣然应允。我作为打杂帮手,为九爷捋条递条。帮手不仅是个力气活,也是个眼色活,需要配合上的默契,粗细长短搭配是有讲究的,这时递条人对编条人的察言观色很重要。递条人往往要在编条人发出指令前把所需条形选择好,这样可使编条人操作起来更加得心应手。我一根一根地递条,九爷一根一根地编条,随着编条人发力强度的不同,我看见九爷每编一根条都本能地呲一次牙,仿佛他的牙齿也在发力,嘴角的皱纹也在发力。只消一会儿的工夫,就有了立锥之地。随着条编面积的不断扩大,楼的雏形开始显现,我也由楼檩上蹲坐转移到楼棚上,行为上不再那样如悬当空小心翼翼,脚下有了踏实感。后来,屋内的光线暗淡了,太阳压着西山顶了,我和九爷的杰作也完成了。九爷让我找了把直尺量了一下,长4米,宽3.5米,整体结构还算周正,像一张偌大的黑色芦席。油灯初上时分,全家人都登上梯子到条编楼上走了一遍,这里踩踩,那里跺跺,别样的心情,别样的喜悦。那一夜,我一张芦苇席一条粗布单在粗糙的条编楼上睡了一宿,一种爽爽的小幸福油然而生。
条编楼是不平整的,需要漫上一层拌了麦秸的黑泥巴做表面处理。很快,家里的粮食搬上去了,杂七杂八的东西也放上去了,屋宽了,一家人的心也宽了。
闲暇,我总爱爬上条编洋槐楼,临窗看小街,有低下头拉平车的,有挑担的,有肩扛镢锄手执镰刀的,熟悉或陌生的身影总是匆匆一闪而过,一波一波涌动着我的遐思。
如今,村子早已旧貌换了新颜,家家独居小楼窗明几净,庭院花草芬芳,赏心悦目。村外曾经荒芜的坡坡岭岭,点缀着桃园竹林梅园等绿色植被,网红路如彩带般蜿蜒其间,时有游人徘徊留恋。2020年,村子还多了一个好听的称号:全国生态文化村。在村庄,没有什么比幸福指数的提升更感人更实在了。偶遇亲友相聚,我总爱把手编洋槐楼的故事讲给那些晚辈们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