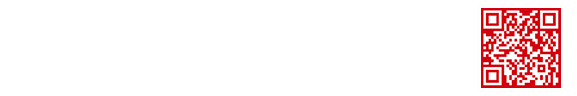别院深深夏席清,石榴开遍透帘明,树荫满地日当午,梦觉流莺时一声。苏舜钦眼里的夏意徘徊于深深别院,藏匿于婆娑树荫,定格于石榴花丛,流连于午睡梦醒时。一千多年过去了,时光的长河冲淡了那个夏日的光景,但冲不淡的,是那片婆娑树荫留在心底的清凉。
木心说:“夏季里的事,多半容易沾随记忆。”小时候,村中的夏来得轻,来得缓,来得温柔,树叶是慢慢长成可供人乘凉厚度的,百花是缓缓开成绚烂模样的,偶尔一阵微风吹过,仿佛是平芜尽处抵赖不肯走的春风,在与你作最后的告别。
初夏之后,一种隆重而热烈的仪式开始了。百花盛开,树荫铺就斑驳地毯,麦穗低头,鸟雀齐鸣,宛如迎接赫赫战功的将军,迎接盛夏这位远道而来的尊贵客人。
盛夏时刻,村中的日光像喝醉酒的莽汉,时而醉倒在一望无垠的麦田,时而卧眠于群峰迭起的远山。犹记得,村口有一小片荷塘,一阵夏风吹过,荷叶随风摇曳。摇曳间,荷花若隐若现,如犹抱琵琶半遮面之少女,颇有周邦彦“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之神韵。
关于盛夏的记忆,还可追溯到汪曾祺《人间草木》中的一段话:西瓜以绳络悬于井中,下午剖食,一刀下去,咔嚓有声,凉气四溢,连眼睛都是凉的。
升起的西瓜、溅起的水花,是当时的盛夏。记得那时,最爱和姥爷下到山沟里玩。姥爷拔葱,我便学着他的模样一起拔,结果不是连根拔起,就是拔不动摔一屁蹲儿,气鼓鼓地站起来,小脸憋得通红。后来才想明白,那也是个生命,在与小小的我较劲呢。从山沟里上来后,缠着姥爷买冰棍。小时候,总爱吃一种叫“绿舌头”的冰棍,软软的、滑滑的,吃得舌心赤绿,弄得浑身都是腻腻滑滑的,回家后被姥姥满院子追着打。那时候,总得意洋洋于姥姥追不上我,后来想想可能她是故意为之……就这样,被那些盛夏抚育的我长大了,像个野孩子般光着膀子在田地里跑着跑着就长大了,长大得猝不及防,甚至来不及跟那些盛夏告别。多年后回头看,最怀念的,还是做田地里的“野孩子”、当姥姥的“淘气包”的那些日子——不是那些夏日动人,而是那些夏日回忆里的烟火气动人。
傍晚村口的家长里短、姥姥手里的大蒲扇、猝不及防的蚊子包和突如其来的大暴雨,都是那个夏天最特别的礼物。那时候的夏日,总是浸泡在各种水里,河水里、雨水里、洗澡水里,还有汗水里,湿漉漉的,冒着热气,如化不开的浓雾萦绕心底,让人难以忘怀。
回忆至此,我才突然意识到,原来有那么多东西,可以形容那时的夏天。看吧,事物都有其超出本身的意义与价值,就像夏天也可以是一份记忆。这个夏季,疫情偶尔在捣乱,日子里有烦恼和无奈,有欢喜和放纵。有时,人们更容易从粗粝的、直接的物质安慰中得到情感的宣泄,而精神层面的追求,似乎成了生活的边缘。也许这个夏天,你未曾在意那山那水那河流,忽略了眼前的草甸、峡谷、杉树、苔藓和一些美丽的花儿,但请别忘记这些灿烂的生命只盛开在这个夏天,这些夏日的美好值得我们留恋。
夏至已过,夏意渐浓。山远光长,日悬不落,心有余闲,品味一粟一羹汤,看尽一花一落叶,兴之所起,良辰孤往,乘兴而至,执杖耘耔。
四时更迭,惟愿盛夏时光停留稍久,在最长的白昼里数一数蝉鸣,在最热烈的岁月里忆一忆俗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