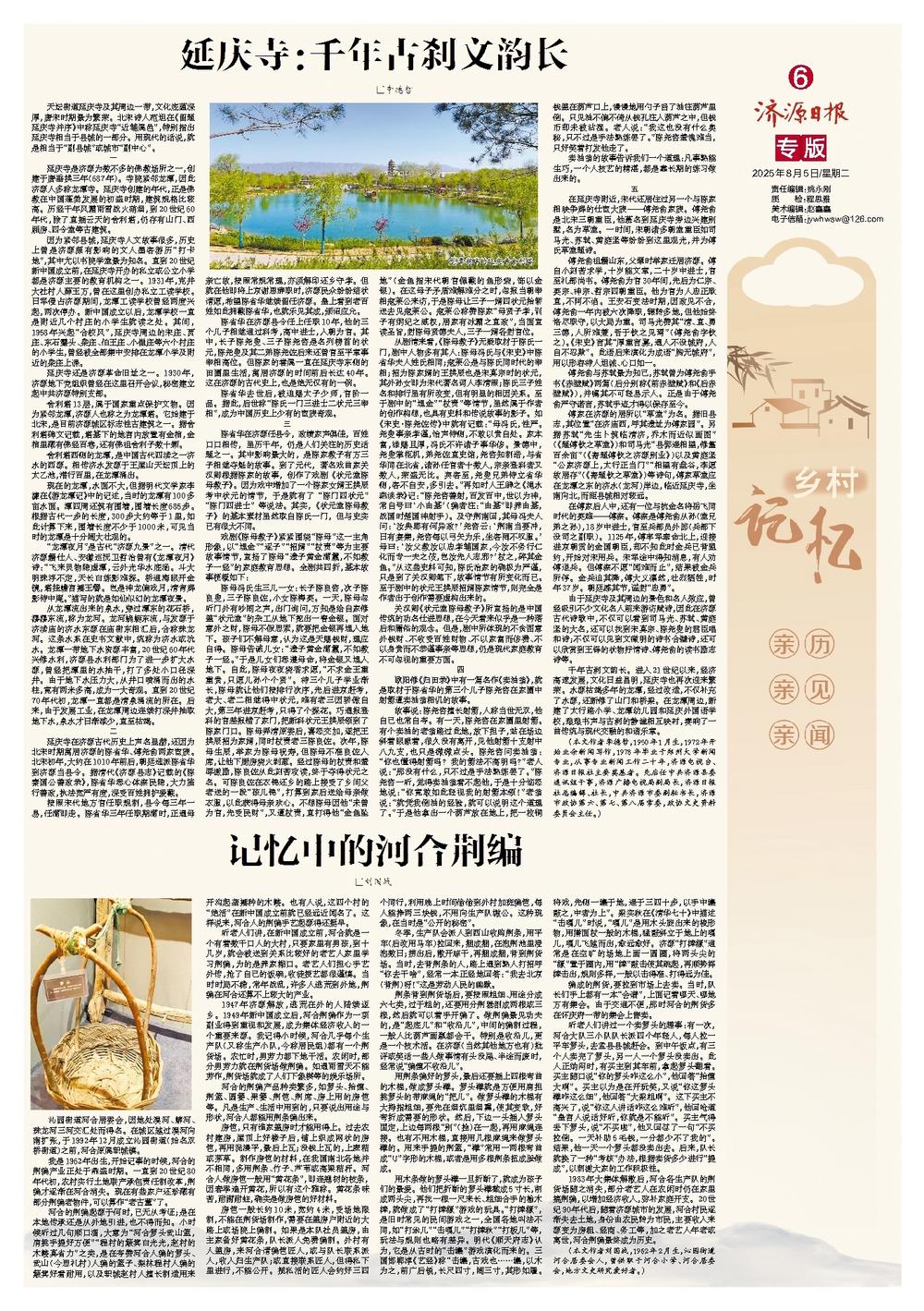沁园街道河合居委会,因地处湨河、蟒河、珠龙河三河交汇处而得名。在城区越过湨河向南扩张,于1992年12月成立沁园街道(始名双桥街道)之前,河合原属轵城镇。
我是1962年出生,开始记事的时候,河合的荆编产业正处于鼎盛时期。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荆编才逐渐在河合消失。现在有些家户还珍藏有部分荆编老物件,可以算作“老古董”了。
河合的荆编起源于何时,已无从考证;是在本地传承还是从外地引进,也不得而知。小时候听过几句顺口溜,大意为“河合箩头武山篮,肩挑手提好方便”“程村的簸箕白光光,赵村的木耧真省力”之类,是在夸赞河合人编的箩头、武山(今思礼村)人编的篮子、梨林程村人编的簸箕好看耐用,以及轵城赵村人擅长制造用来开沟起垄播种的木耧。也有人说,这四个村的“绝活”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已经远近闻名了。这样说来,河合人的荆编手艺起源得还挺早。
听老人们讲,在新中国成立前,河合就是一个有着数千口人的大村,只要家里有男孩,到十几岁,就会被送到关系比较好的老艺人家里学习荆编,为的是养家糊口。老艺人们担心手艺外传,抢了自己的饭碗,收徒授艺都很谨慎。当时时局不稳,常年战乱,许多人逃荒到外地,荆编在河合还算不上较大的产业。
1947年济源解放,逃荒在外的人陆续返乡。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河合荆编作为一项副业得到重视和发展,成为集体经济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我记得小时候,河合几乎每个生产队(又称生产小队,今称居民组)都有一个荆货场。农忙时,男劳力都下地干活。农闲时,部分男劳力就在荆货场做荆编。如遇雨雪天不能劳作,荆货场就成了人们下象棋等的娱乐场所。
河合的荆编产品种类繁多,如箩头、抬筐、荆篮、圆篓、果篓、荆笆、荆席、房上用的房笆等。凡是生产、生活中用到的,只要说出用途与形状,河合人都能用荆条编出来。
房笆,只有谁家盖房时才能用得上。过去农村建房,屋顶上好椽子后,铺上织成网状的房笆,再用泥漫平,最后上瓦;没钱上瓦的,上麦秸或茅草。制作房笆的材料,在我国南北各地并不相同,多用荆条、竹子、芦苇或高粱秸秆。河合人做房笆一般用“黄花条”,即连翘树的枝条,因春季遍开黄花,所以有这个雅称。黄花条味苦,耐腐耐蛀,确实是做房笆的好材料。
房笆一般长约10米,宽约4米,受场地限制,不能在荆货场制作,需要在盖房户附近的大路上或场院上编制。如果是本队社员盖房,由主家备好黄花条,队长派人免费编制。外村有人盖房,来河合请编笆匠人,或与队长联系派人,收入归生产队;或直接联系匠人,但得私下里进行,不能公开。揽私活的匠人会约好三四个同行,利用晚上时间偷偷到外村加班编笆,每人能挣两三块钱,不用向生产队缴公。这种现象,在当时是“公开的秘密”。
冬季,生产队会派人到西山收购荆条,用平车(后改用马车)拉回来,捆成捆,在泡荆池里浸泡数日;捞出后,散开晾干,再捆成捆,背到荆货场。当时,去背荆条的人,路上遇到熟人打招呼“你去干啥”,经常一本正经地回答:“我去北京(背荆)呀!”这是劳动人民的幽默。
荆条背到荆货场后,要按照粗细、用途分成六七类,过于粗的,还要用分荆器剖成两根或三根,然后就可以着手开编了。做荆编最见功夫的,是“起底儿”和“收沿儿”,中间的编制过程,一般人比葫芦画瓢都会干。特别是收沿儿,更是一个技术活。在济源(当然其他地方也有)批评或笑话一些人做事情有头没尾、半途而废时,经常说“编筐不收沿儿”。
用荆条编好的箩头,最后还要插上四根弯曲的木棍,做成箩头襻。箩头襻就是方便用扁担挑箩头的带麻绳的“把儿”。做箩头襻的木棍有大拇指粗细,要先在烟坑里烟熏,使其变软,好弯折成需要的形状。然后,下边一头插入箩头固定,上边每两根“别”(拴)在一起,再用麻绳连接。也有不用木棍,直接用几根麻绳来做箩头襻的。用来手提的荆篮,“襻”常用一两根弯曲成“U”字形的木棍,或者是用多根荆条扭成股做成。
用木条做的箩头襻一旦折断了,就成为孩子们的最爱。他们把折断的箩头襻截成5寸长,削成两头尖,再找一根一尺来长、粗细合手的榆木棒,就做成了“打棒橛”游戏的玩具。“打棒橛”,是旧时常见的民间游戏之一,全国各地叫法不同,如“打尜儿”“击嘎儿”“打棒秋”“打板儿”等,玩法与规则也略有差异。明代《顺天府志》认为,它是从古时的“击壤”游戏演化而来的。三国邯郸淳《艺经》称“击壤,古戏也……壤,以木为之,前广后锐,长尺四寸,阔三寸,其形如履。将戏,先侧一壤于地,遥于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敲之,中者为上”。梁实秋在《清华七十》中描述“击嘎儿”时说,“嘎儿”是用木头旋出来的梭形物,用擀面杖一般的木棍,猛敲斜立于地上的嘎儿,嘎儿飞越而出,愈远愈好。济源“打棒橛”通常是在空旷的场地上画一圆圈,将两头尖的“橛”置于圈内,用“棒”敲击使其跳起,再顺势挥棒击出,规则多样,一般以击得准、打得远为佳。
编成的荆货,要拉到市场上去卖。当时,队长们手上都有一本“会谱”,上面记着哪天、哪地方有集会。由于交通不便,那时河合的荆货多在怀庆府一带的集会上售卖。
听老人们讲过一个卖箩头的趣事:有一次,河合大队三小队队长派四个年轻人,每人拉一平车箩头,去孟县县城赶会。到中午饭点,有三个人卖完了箩头,另一人一个箩头没卖出。此人正纳闷时,有买主到其车前,拿起箩头翻看。买主随口说“你的箩头咋这么小”,他回答“抬筐大啊”。买主以为是在开玩笑,又说“你这箩头襻咋这么细”,他回答“大梁粗啊”。这下买主不高兴了,说“你这人讲话咋这么难听”,他回呛道“皇宫人说话好听,你就是不能听”。买主气得丢下箩头,说“不买啦”,他又回怼了一句“不买拉倒。一天补助5毛钱,一分都少不了我的”。结果,他一天一个箩头都没卖出去。后来,队长就换了一种“考核”办法,根据卖货多少进行“提成”,以刺激大家的工作积极性。
1983年大集体解散后,河合各生产队的荆货场随之消失,部分老艺人在农闲时仍在家里搞荆编,以增加经济收入,弥补家庭开支。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济源城市的发展,河合村民逐渐失去土地,身份由农民转为市民,主要收入来源变为房租、经商、务工等,加之老艺人年老或离世,河合荆编最终成为历史。
(本文作者刘国战,1962年2月生,沁园街道河合居委会人,曾供职于河合小学、河合居委会,地方文史研究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