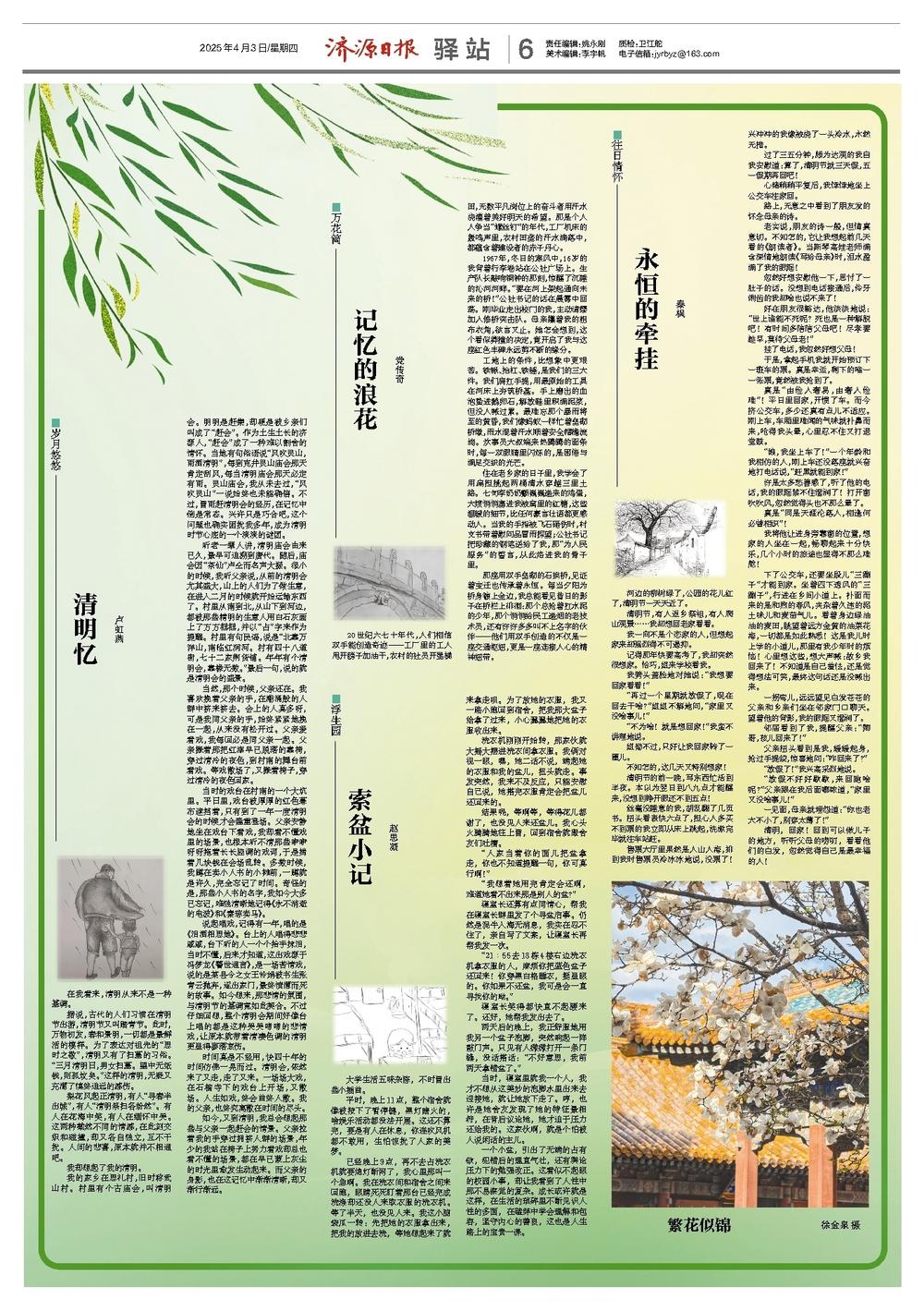在我看来,清明从来不是一种基调。
据说,古代的人们习惯在清明节出游,清明节又叫踏青节。此时,万物初发,春和景明,一切都是最鲜活的模样。为了表达对祖先的“思时之敬”,清明又有了扫墓的习俗。“三月清明日,男女扫墓。望中无纸钱,则孤坟矣。”这样的清明,无疑又充满了慎终追远的感伤。
梨花风起正清明,有人“寻春半出城”,有人“清明祭扫各纷然”。有人在花海中笑,有人在缅怀中哭。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情感,在此刻交织和碰撞,却又各自独立,互不干扰。人间的悲喜,原本就并不相通吧。
我却想起了我的清明。
我的家乡在思礼村,旧时称武山村。村里有个古庙会,叫清明会。明明是赶集,却硬是被乡亲们叫成了“赶会”。作为土生土长的济源人,“赶会”成了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怀。当地有句俗语说“风吹灵山,雨洒清明”,每到克井灵山庙会那天肯定刮风,每当清明庙会那天必定有雨。灵山庙会,我从未去过,“风吹灵山”一说始终也未能确信。不过,冒雨赶清明会的经历,在记忆中倒是常态。兴许只是巧合吧,这个问题也确实困扰我多年,成为清明时节心底的一个淡淡的谜团。
听老一辈人讲,清明庙会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唐代。随后,庙会因“茶仙”卢仝而名声大振。很小的时候,我听父亲说,从前的清明会尤其盛大,山上的人们为了做生意,在进入二月的时候就开始运输东西了。村里从南到北,从山下到河边,都被那些精明的生意人用白石灰画上了方方框框,并以“占”字来作为提醒。村里有句民谣,说是“北靠万洋山,南临红涧河。村有四十八道街,七十二家荆货铺。年年有个清明会,靠椽无数。”最后一句,说的就是清明会的盛景。
当然,那个时候,父亲还在。我喜欢挽着父亲的手,在潮涌般的人群中挤来挤去。会上的人真多呀,可是我同父亲的手,始终紧紧地挽在一起,从来没有松开过。父亲爱看戏,我每回必是同父亲一起。父亲搬着那把红漆早已脱落的靠椅,穿过清冷的夜色,到村南的舞台前看戏。等戏散场了,又搬着椅子,穿过清冷的夜色回家。
当时的戏台在村南的一个大坑里。平日里,戏台被厚厚的红色幕布遮挡着,只有到了一年一度清明会的时候才会隆重登场。父亲安静地坐在戏台下看戏,我却看不懂戏里的场景,也根本听不清那些咿咿呀呀拖着长长腔调的戏词,于是揣着几块钱在会场乱转。多数时候,我蹲在卖小人书的小摊前,一蹲就是许久,完全忘记了时间。奇怪的是,那些小人书的名字,我如今大多已忘记,唯独清晰地记得《永不消逝的电波》和《秦琼卖马》。
说起唱戏,记得有一年,唱的是《泪洒相思地》。台上的人唱得悲悲戚戚,台下听的人一个个抬手抹泪,当时不懂,后来才知道,这出戏源于冯梦龙《警世通言》,是一场苦情戏,说的是某县令之女王怜娟被书生张青云抛弃,逐出家门,最终愤懑而死的故事。如今想来,那悲情的氛围,与清明节的基调竟如此契合。不过仔细回想,整个清明会期间好像台上唱的都是这种哭哭啼啼的悲情戏,让原本就带着清凄色调的清明更显得寥落哀伤。
时间真是不经用,快四十年的时间仿佛一晃而过。清明会,依然来了又走,走了又来。一场场大戏,在石榴寺下的戏台上开场,又散场。人生如戏,终会曲终人散。我的父亲,也终究离散在时间的尽头。
如今,又到清明,我总会想起那些与父亲一起赶会的情景。父亲拉着我的手穿过拥挤人群的场景,年少的我站在椅子上努力看戏却总也看不懂的场景,都在早已蒙上灰尘的时光里愈发生动起来。而父亲的身影,也在这记忆中渐渐清晰,却又渐行渐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