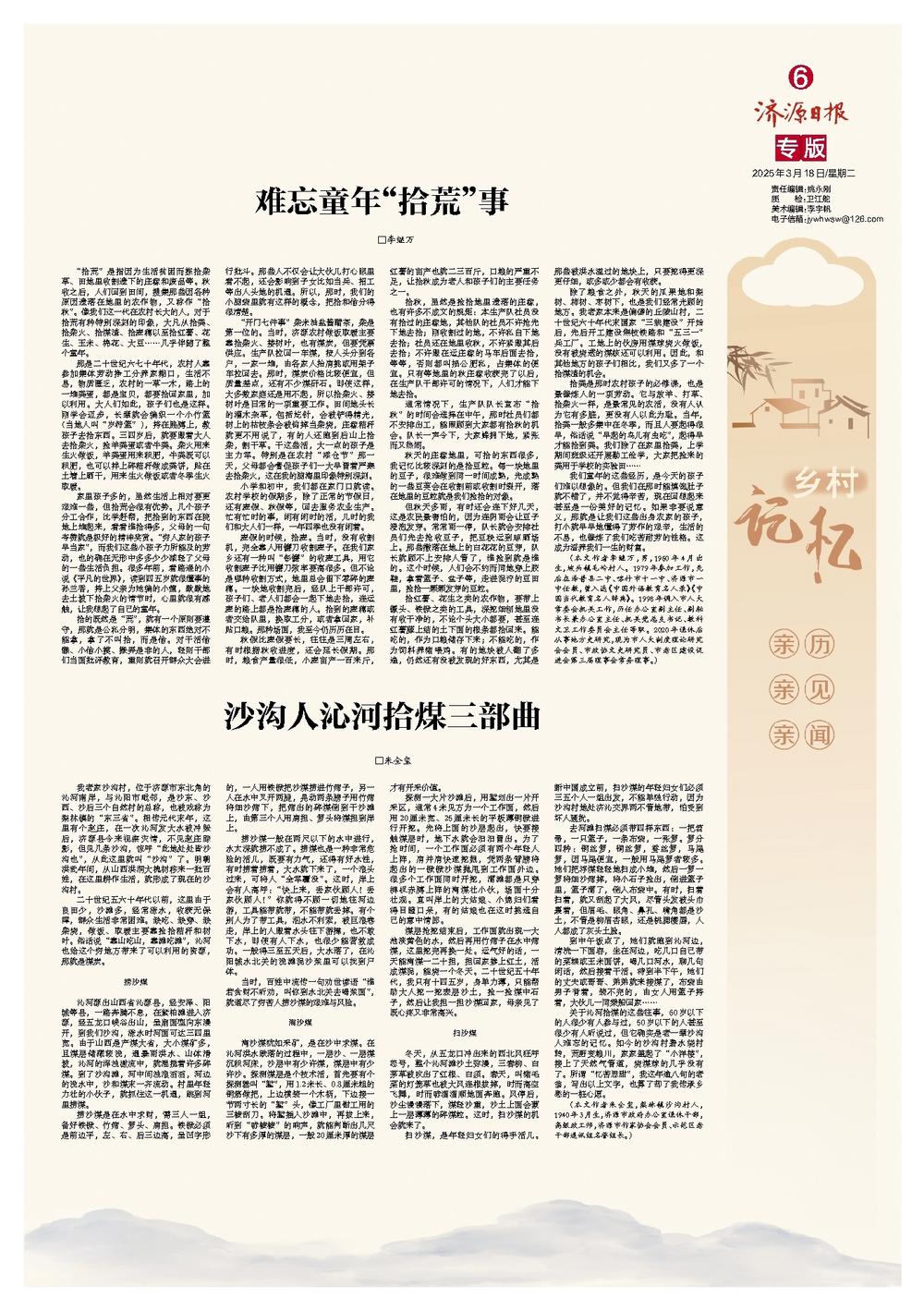我老家沙沟村,位于济源市东北角的沁河南岸,与沁阳市毗邻,是沙东、沙西、沙后三个自然村的总称,也被戏称为梨林镇的“东三省”。相传元代末年,这里有个赵庄,在一次沁河发大水被冲毁后,济源县令来视察灾情,不见赵庄踪影,但见几条沙沟,惊呼“此地处处皆沙沟也”,从此这里就叫“沙沟”了。明朝洪武年间,从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来一批百姓,在这里耕作生活,就形成了现在的沙沟村。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前,这里由于良田少,沙滩多,经常涨水,收获无保障,群众生活非常困难。缺吃、缺穿、缺柴烧,做饭、取暖主要靠捡拾秸秆和树叶。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滩吃滩”,沁河也给这个穷地方带来了可以利用的资源,那就是煤炭。
捞沙煤
沁河源出山西省沁源县,经安泽、阳城等县,一路奔腾不息,在紫柏滩进入济源,经五龙口峡谷出山,呈扇面型向东漫开,到我们沙沟,涨水时河面可达三四里宽。由于山西是产煤大省,大小煤矿多,且煤层储藏较浅,遇暴雨洪水、山体滑坡,沁河的浑浊激流中,就混搅着许多碎煤。到了沙沟滩,河中间浊浪滔滔,河边的浅水中,沙和煤末一齐流动。村里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就抓住这一机遇,跳到河里捞煤。
捞沙煤是在水中求财,需三人一组,备好铁锨、竹筛、箩头、扁担。铁锨必须是前边平,左、右、后三边高,呈凹字形的,一人用铁锨把沙煤捞进竹筛子,另一人在水中叉开两腿,晃动两条膀子用竹筛将细沙筛下,把筛出的碎煤倒到干沙滩上,由第三个人用扁担、箩头将煤担到岸上。
捞沙煤一般在两尺以下的水中进行,水太深就捞不成了。捞煤也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活儿,既要有力气,还得有好水性,有时捞着捞着,大水就下来了,一个浪头过来,可将人“全军覆没”。这时,岸上会有人高呼:“快上来,丢家伙顾人!丢家伙顾人!”你就得不顾一切地往河边游,工具能带就带,不能带就丢掉。有个别人为了带工具,泅水不利索,被巨浪卷走,岸上的人跟着水头往下游撵,也不敢下水,即使有人下水,也很少能营救成功。一般得三至五天后,大水落了,在沁阳城水北关的浅滩泥沙浆里可以找到尸体。
当时,百姓中流传一句劝世谚语“谁若贪财不听劝,叫你到水北关去喝浆面”,就道尽了穷苦人捞沙煤的艰难与风险。
淘沙煤
淘沙煤犹如采矿,是在沙中求煤。在沁河洪水跌落的过程中,一层沙、一层煤沉积河床,沙层中有少许煤,煤层中有少许沙。探测煤层是个技术活,首先要有个探测器叫“錾”,用1.2米长、0.8厘米粗的钢筋做把,上边横装一个木柄,下边接一节两寸长的“錾”头,像工厂里钳工用的三棱刮刀。将錾插入沙滩中,再拔上来,听到“哧棱棱”的响声,就能判断出几尺沙下有多厚的煤层,一般20厘米厚的煤层才有开采价值。
探测一大片沙滩后,用錾划出一片开采区,通常4米见方为一个工作面,然后用20厘米宽、25厘米长的平板薄钢锨进行开挖。先将上面的沙层起出,快要接触煤层时,地下水就会汩汩冒出。为了抢时间,一个工作面必须有两个年轻人上阵,肩并肩快速挖掘,凭两条臂膀将起出的一锨锨沙煤抛甩到工作面外边。很多个工作面同时开挖,满滩都是只穿裤衩赤膊上阵的淘煤壮小伙,场面十分壮观。直叫岸上的大姑娘、小媳妇们看得目瞪口呆,有的姑娘也在这时挑选自己的意中情郎。
煤层抢挖结束后,工作面就出现一大池淡黄色的水,然后再用竹筛子在水中筛煤,这里挖完再换一处。运气好的话,一天能淘煤一二十担,担回家掺上红土,活成煤泥,能烧一个冬天。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只有十四五岁,身单力薄,只能帮助大人挖一挖表层沙土,捡一捡煤中石子,然后让我担一担沙煤回家,母亲见了既心疼又非常高兴。
扫沙煤
冬天,从五龙口冲出来的西北风狂呼怒号,整个沁河滩沙土弥漫,三春柳、白茅草被吹出了红根、白须。春天,叫猪毛菜的灯笼草也被大风连根拔掉,时而高空飞舞,时而哧溜溜顺地面奔跑。风停后,沙尘慢慢落下,煤轻沙重,沙土上面会蒙上一层薄薄的碎煤粒。这时,扫沙煤的机会就来了。
扫沙煤,是年轻妇女们的得手活儿。新中国成立前,扫沙煤的年轻妇女们必须三五个人一组出发,不能单独行动,因为沙沟村地处济沁交界两不管地带,怕受到坏人骚扰。
去河滩扫煤必须带四样东西:一把笤帚,一只篮子,一条布袋,一张箩。箩分四种:钢丝箩,铜丝箩,蚕丝箩,马尾箩,因马尾便宜,一般用马尾箩者较多。她们把浮煤轻轻地扫成小堆,然后一箩一箩将细沙筛掉,将小石子捡出,倒进篮子里,篮子满了,倒入布袋中。有时,扫着扫着,就又刮起了大风,尽管头发被头巾裹着,但眉毛、眼角、鼻孔、嘴角都是沙土,不管是柳眉杏眼,还是桃腮樱唇,人人都成了灰头土脸。
到中午饭点了,她们就跑到沁河边,清洗一下面容,坐在河边,吃几口自己带的菜糕或玉米面饼,喝几口河水,聊几句闲话,然后接着干活。待到半下午,她们的丈夫或哥哥、弟弟就来接煤了,布袋由男子背着,装不完的,由女人用篮子挎着,大伙儿一同乘船回家……
关于沁河拾煤的这些往事,60岁以下的人很少有人参与过,50岁以下的人甚至很少有人听说过,但它确实是老一辈沙沟人难忘的记忆。如今的沙沟村碧水绕村转,荒野变粮川,家家盖起了“小洋楼”,接上了天然气管道,烧煤球的几乎没有了。所谓“忆苦思甜”,我这年逾八旬的老翁,写出以上文字,也算了却了我传承乡愁的一桩心愿。
(本文作者朱全玺,梨林镇沙沟村人,1940年3月生,济源市政府办公室退休干部,高级政工师,济源市作家协会会员、示范区老干部通讯组名誉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