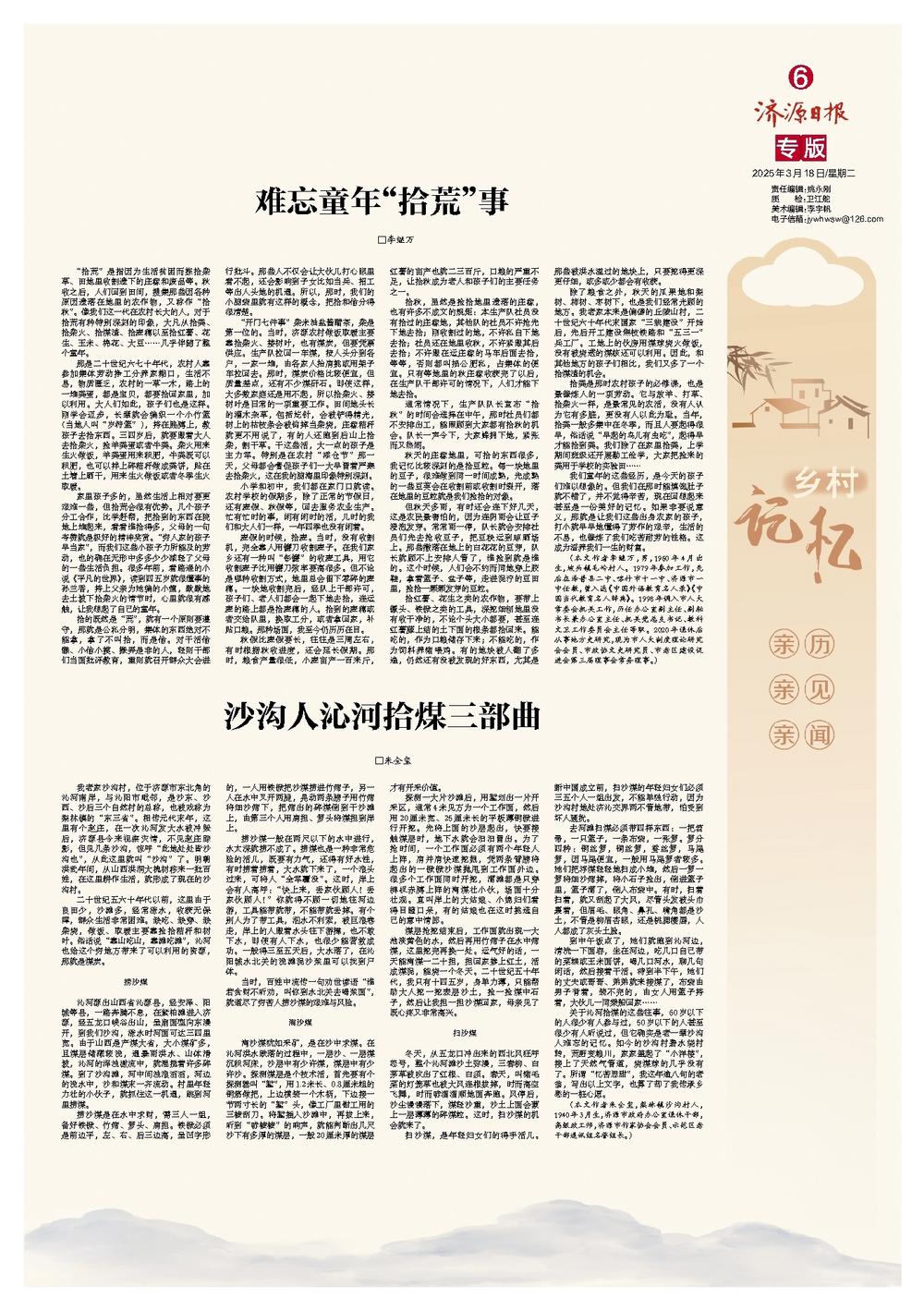“拾荒”是指因为生活贫困而拣拾柴草、田地里收割遗下的庄稼和废品等。秋收之后,人们回到田间,搜集那些因各种原因遗落在地里的农作物,又称作“拾秋”。像我们这一代在农村长大的人,对于拾荒有种特别深刻的印象,大凡从拾粪、拾柴火、拾煤渣、拾麦穗以至拾红薯、花生、玉米、棉花、大豆……几乎伴随了整个童年。
那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人靠参加集体劳动挣工分养家糊口,生活不易,物质匮乏,农村的一草一木,路上的一堆粪蛋,都是宝贝,都要拾回家里,加以利用。大人们如此,孩子们也是这样。刚学会迈步,长辈就会编织一个小竹篮(当地人叫“岁符篮”),挎在胳膊上,教孩子去拾东西。三四岁后,就要跟着大人去拾柴火,捡羊粪蛋或者牛粪。柴火用来生火做饭,羊粪蛋用来积肥,牛粪既可以积肥,也可以拌上碎秸秆做成粪饼,贴在土墙上晒干,用来生火做饭或者冬季生火取暖。
家里孩子多的,虽然生活上相对要更艰难一些,但拾荒会很有优势。几个孩子分工合作,比学赶帮,把拾到的东西在院地上堆起来,看看谁拾得多,父母的一句夸赞就是极好的精神奖赏。“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而我们这些小孩子力所能及的劳动,也的确在无形中多多少少减轻了父母的一些生活负担。很多年前,看路遥的小说《平凡的世界》,读到四五岁就很懂事的孙兰香,挎上父亲为她编的小筐,默默地去土坡下拾柴火的情节时,心里就很有感触,让我想起了自己的童年。
拾的既然是“荒”,就有一个原则要遵守,那就是公私分明,集体的东西绝对不能拿,拿了不叫拾,而是偷。对干活偷懒、小偷小摸、搬弄是非的人,轻则干部们当面批评教育,重则就召开群众大会进行批斗。那些人不仅会让大伙儿打心眼里看不起,还会影响到子女比如当兵、招工等出人头地的机遇。所以,那时,我们的小脑袋里就有这样的概念,把拾和偷分得很清楚。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柴是第一位的。当时,济源农村做饭取暖主要靠拾柴火、搂树叶,也有煤炭,但要凭票供应。生产队拉回一车煤,按人头分到各户,一家一堆,由各家人抬肩挑或用架子车拉回去。那时,煤炭价格比较便宜,但质量差点,还有不少煤矸石。即使这样,大多数家庭还是用不起,所以拾柴火、搂树叶是日常的一项重要工作。田间地头长的灌木杂草,包括圪针,会被铲得精光,树上的枯枝条会被钩掉当柴烧,庄稼秸秆就更不用说了,有的人还跑到后山上拾柴,割干草。干这些活,大一点的孩子是主力军。特别是在农村“添仓节”那一天,父母都会督促孩子们一大早冒着严寒去拾柴火,这在我的脑海里印象特别深刻。
小学和初中,我们都在家门口就读。农村学校的假期多,除了正常的节假日,还有麦假、秋假等,回去服务农业生产。忙有忙时的事,闲有闲时的活,儿时的我们和大人们一样,一年四季也没有闲着。
麦假的时候,拾麦。当时,没有收割机,完全靠人用镰刀收割麦子。在我们家乡还有一种叫“钐镰”的收麦工具,用它收割麦子比用镰刀效率要高很多。但不论是哪种收割方式,地里总会留下零碎的麦穗。一块地收割完后,经队上干部许可,孩子们、老人们都会一起下地去拾,连运麦的路上都是拾麦穗的人。拾到的麦穗或者交给队里,换取工分,或者拿回家,补贴口粮。那种场面,我至今仍历历在目。
秋假比麦假要长,往往是三周左右,有时根据秋收进度,还会延长假期。那时,粮食产量很低,小麦亩产一百来斤,红薯的亩产也就二三百斤,口粮的严重不足,让拾秋成为老人和孩子们的主要任务之一。
拾秋,虽然是捡拾地里遗落的庄稼,也有许多不成文的规矩:本生产队社员没有拾过的庄稼地,其他队的社员不许抢先下地去拾;刚收割过的地,不许私自下地去拾;社员还在地里收秋,不许紧跟其后去拾;不许跟在运庄稼的马车后面去拾,等等,否则都叫损公肥私,占集体的便宜。只有等地里的秋庄稼收获完了以后,在生产队干部许可的情况下,人们才能下地去拾。
通常情况下,生产队队长宣布“拾秋”的时间会选择在中午,那时社员们都不安排出工,能照顾到大家都有拾秋的机会。队长一声令下,大家蜂拥下地,紧张而又热闹。
秋天的庄稼地里,可拾的东西很多,我记忆比较深刻的是拾豆粒。每一块地里的豆子,很难做到同一时间成熟,先成熟的一些豆荚会在收割前或收割时裂开,落在地里的豆粒就是我们捡拾的对象。
但秋天多雨,有时还会连下好几天,这是农民最害怕的,因为连阴雨会让豆子浸泡发芽。常常雨一停,队长就会安排社员们先去抢收豆子,把豆秧运到晾晒场上。那些撒落在地上的白花花的豆芽,队长就顾不上安排人管了,谁捡到就是谁的。这个时候,人们会不约而同地穿上胶鞋,拿着篮子、盆子等,走进泥泞的豆田里,捡拾一颗颗发芽的豆粒。
拾红薯、花生之类的农作物,要带上镢头、铁锨之类的工具,深挖细刨地里没有收干净的,不论个头大小都要,甚至连红薯藤上结的土下面的根条都拾回来。能吃的,作为口粮储存下来;不能吃的,作为饲料养猪喂鸡。有的地块被人翻了多遍,仍然还有没被发现的好东西,尤其是那些被洪水溢过的地块上,只要挖得更深更仔细,或多或少都会有收获。
除了粮食之外,秋天的瓜果地和梨树、柿树、枣树下,也是我们经常光顾的地方。我老家本来是偏僻的丘陵山村,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国家“三线建设”开始后,先后开工建设焦枝铁路和“五三一”兵工厂。工地上的伙房用煤球烧火做饭,没有被烧透的煤核还可以利用。因此,和其他地方的孩子们相比,我们又多了一个拾煤渣的机会。
拾粪是那时农村孩子的必修课,也是最锻炼人的一项劳动。它与放羊、打草、拾柴火一样,是最常见的农活,没有人认为它有多脏,更没有人以此为耻。当年,拾粪一般多集中在冬季,而且人要起得很早,俗话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起得早才能拾到粪。我们除了在家里拾粪,上学期间班级还开展勤工俭学,大家把捡来的粪用于学校的实验田……
我们童年的这些经历,是今天的孩子们难以想象的。但我们在那时能填饱肚子就不错了,并不觉得辛苦,现在回想起来甚至是一份美好的记忆。如果非要说意义,那就是让我们这些出身农家的孩子,打小就早早地懂得了劳作的艰辛,生活的不易,也锻炼了我们吃苦耐劳的性格。这成为滋养我们一生的财富。
(本文作者李继万,男,1960年4月出生,坡头镇毛岭村人。1979年参加工作,先后在泽普县二中、喀什市十一中、济源市一中任教,曾入选《中国外语教育名人录》《中国当代教育名人辞典》。1998年调入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工作,历任办公室副主任、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机关党总支书记、教科文卫工作委员会主任等职。2020年退休后从事地方史研究,现为市人大制度理论研究会会员、市政协文史研究员、市老区建设促进会第三届理事会常务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