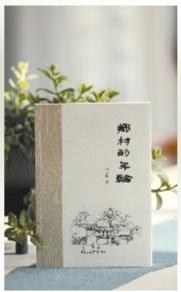一
姚永刚的书稿放在这里有一段时间了,这一年里我有较重的创作任务,一切影响此任务的都不得不推掉,但是永刚很是执着,一直想让为他的这本集子写点感想,哪怕多等一等。从与永刚的接触中,我觉得他是一个质朴的人,没有多少言语,做事情也比较严谨,书稿传过来,从没有催问过一声,甚至微信上连一句问候也没有。我知道他是不好意思打搅,而这也就更是让我惦记着这么一件事,写作的间隙,会时不时打开放在桌面上的书稿看上一眼。说不分心是假,还是要想着他都写了什么,他的关注点在哪里,他的写作有哪些特色,他究竟是怎样的人,怎样的心态,怎样的情怀,有没有写作潜力,是给予肯定,还是挑一挑不足。
说实在的,大凡人家让写个序放在前面,就是想要点鼓励,出一本书不容易,而且写作这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就是讲出来,也不一定是对的。何况每个人的写作(包括我自己)都有着这样那样的毛病,有毛病是常事,没有毛病倒是怪事了。由此说,我是带着欣赏的眼光去看待永刚的写作,这种心态不管好或不好,于我来说是愉快的。何况永刚的所写大部分还是我喜欢的。
永刚是豫东人,在郑州上的大学,工作却是去了豫西的济源。豫东和豫西是两个地理概念,豫东方圆一片辽阔沃野,豫西则到处是苍莽群山。这对于永刚来说是一件好事情,不同的人生阅历,会完全渗透到创作中去。因此永刚就有了两种生命体验,这在这部集子里集中地展现出来。他将一部分笔墨述写自己家乡的生活生物,一部分笔墨描画王屋山的风景风情,这两部分情绪交叉,带有着永刚对世事人生的看法,从而也是对于写作的提示与提醒。还有一少部分,写了世事的见闻与观感。整体来看,永刚知道在哪里用笔与用情,知道一个写作者的专注与专心。
二
我曾在《散文时代》一书中写道:“生活离不开味道,好酒的味道,香烟的味道;爱情的味道,婚姻的味道;寒冷的味道,幸福的味道。没有了味道,一切就茫然无觉。文学也属人们生活中的内容,那么,散文的味道呢?散文的味道,应该是那种本真的内在的,富有韵味的充满美感的,意趣横生的妙不可言的,饱含哲理的意象纷呈的。读散文亦当读味道,从中品咂出某种快感的东西。这也就是散文的意义,一篇散文,如果让人感觉不出什么味道——哪怕是痛苦的味道,这篇散文还有什么意义呢?”我引说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永刚的散文,是有着我们想要的味道的。
“朝阳刚过山头,红霞里,葡萄架上紫色玛瑙水灵泛光,旁边的南瓜绿叶上,露珠晶莹透亮,打着转,似落未落。这个农家的小院里,高大的山楂树枝繁叶茂,挂满果实,一嘟噜一嘟噜的,沉甸甸地越过围墙。浅蓝色的晨空里,就绽开了无数的红灯笼。炊烟徐徐升起,韭菜的辛辣,混合着麦香,在院落上空四散漫延。”这是《乡村的表情》中的描写。
“皂荚树下,是村里最大的饭场。粗壮的一股树杈上,悬挂着一口古钟,是开村民大会时用的“发令枪”。所以,这个饭场,不单单是吃饭的场所,也是村里的行政中心。偶尔的一次会议,树下黑压压一片,席地而坐满了人。许多政令村规,就从这里飘向村里的角角落落。”这是《乡村的年轮》里的述说。
“石桥,曲水,抱村而流。地远春就宁,天籁之音,尽宜入耳入心。水是砚瓦河的水,桥是砚瓦河的桥。溪上无人喧,鱼自水面行。寻石磴斜转,断径之处,自然而然,现出荒园。土房土墙的小宅,小茅曲篱寂寂然,不见犬吠与鸡羊,不见诗词里半掩的柴门,只有悬藤的疏篱和北窗下的杈镰,刻着农耕文明的印记。”这是《大地的名片》中的刻画。
细致的展现,还可见《乡情》,永刚写爷爷开着老年代步车,“我”是他唯一的乘客。爷孙俩在农村集会上过足了新奇之瘾。回来时,热情的爷爷还捎带了邻村的一位老人,老人几次要下车走回去,爷爷却坚持把车一直开到老人的院门口。这给作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历经风雨的情谊,胜过陈年的佳酿。那种豁达与包容,质朴与厚道,是世间所有情感中最为醇美的一种情愫,作者写道:“走出很远了,我回头,看见那位老人微弓着脊背,站在那里,依然缓缓地挥手致别致谢。就在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情到老年才至纯至真,可尊可敬。那份历经风雨的情谊,意味更悠长,胜过陈年的佳酿。”
我喜欢这样的文字,不紧不慢的,悠悠荡荡的,曲曲弯弯的,缠缠绵绵的。这绝对不是抒情特浓诗意特重的那种写作,这是一种带有着乡间泥土味道的自然的写作。
人们推崇孙犁、沈从文、汪曾祺,是因为他们的文字背后带给我们诸多东西,我们有时会觉得那些文字很顺畅,写作起来方明白,那是一个大师的功夫。看似平常,实则操练良久,训练有素。
三
中国的文学中有一个深厚的乡愁传统,无论我们走出多远,那份不变的乡情乡音,都会深深地镌刻在我们的记忆中。乡愁也是永刚不变的精神家园和心灵寄托,乡愁不是愁绪,而是对故乡以及故乡一般的乡村的感怀与牵绊、倾心与关注。
比如《乡村的品格》,作者细腻地写了一个“一脚踏两省,鸡鸣听四县”的小山村:艳丽张扬或韬光养晦的野花,挂满红灯笼的柿子树,顶着绿缨的大萝卜,滴着露水的长豆角,夹杂在构树椿树里的灰白的房屋,以及每家都有的石磨盘。其中有不少的小勾小描,如:“青石小路串起的灰石小巷,在或平行或相交的院墙间穿梭。石巷幽静,穿行其间,声嗡韵笃,久不停息。院墙不高,或石块随意围成,或朽木枯枝茬起。似有亦无的围墙,不过起个边界作用,并不防人防心。”“村后的山泉天长日久,在石板路上凿出一条深沟,先民用石块砌岸,依着狭长的岸堤,梯田一样筑起坚固若磐的石屋……河床时而浅且开阔,开阔处有村妇抡槌浣衣,皂荚白沫如鱼吐泡泡;时而窄且幽深,岸壁如削,危乎骇乎,只闻訇然水声而不见底。水动石静,动静相宜,生生不息。”细致的乡村特质,引出了后面好客的主人及迷人的场景。
《乡村的化石》同《乡村的品格》异曲同工,展现出一幅木刻似的乡俗画,柴门、古槐、花狗、麻鸡、彩蝶与窑洞形成对应之美,其中写老夫妇的一段,格外细腻,将山人的实诚与厚道真实地展现,那种天然自带的禀赋,让作者联想到豫东平原的乡邻。
《塬上唢呐》写一位陕西杨凌的乡村唢呐手,西北高原的光棍汉老胡“一飞冲天的唢呐声,就是一桩喜事的报幕员”。老胡的唢呐与老胡的为人牵引人心。
还有《淘陶》,一个荒废的土屋里,有了出乎意料的收获,不仅发现残破不堪的土屋,曾是当年的山乡闺阁,而且闺阁的檐下,还有一只从灰土里露出的陶罐。永刚在文中感叹:当年这司空见惯的寻常物件,蕴藏着一个山乡农家几代人的生活密码。这只陶罐,应该有某种标本意义,应该有许多故事亟待探寻。
永刚善于观察,并精于归纳,《古意的村落》,写的是王屋山中的小沟背,小沟背的鲜活、古朴、自然绘成了一幅风俗画。画中有石:“卧居河床的石头,或如巨船,或如垒卵,或彩纹逶迤,或形态怪异。”画中有水:“水从石间析出,青草掩石,水面渐次开阔,聚成小洼。”“随河床跌宕奔流,该转时就转,该直时就直,腾起的浪花与薄雾,缭绕着五彩巨石的心扉。”画中有远景:“山野里,嫩叶初茂。山崖上,鹅黄团团簇簇,兀自吐艳……”有近景:红白相间的桃花、抱石而生的老树,泛着羞怯新绿的丛林与灌木。有特写:带有着大山秉性的石砖、石墙、石磙、石碾、石磨。寂幽的鸟叫、鸡鸣。笃实的牛羊、黄狗。悬垂的独木、栈道、铁索吊桥。荷锄而归的女主人。
除了以上所举,《乡村的片段》《乡村的年轮》《乡村的表情》,无一不是接地气的文字。
四
永刚的目光不只留驻在豫东平原或王屋山下,他有意拓宽自己的视野,并且积极对待每一次出行,尤其是那些有着丰厚的地理人文的所在,他都能用心踏访。也就是说,在远离烦扰的同时,着意发现一些质朴的美善的元素,引发心灵的共鸣。你看,省内最高的山峰老鸦岔垴、大唐高僧玄奘的故居、风格独特的客家土楼,景色奇异的凤凰古城、秀色可餐的鹭岛厦门、迷人眼目的苍山武夷,无不成为他施展文字、释放情怀的妙境。
轵城是一座个性之城,周襄王把阳樊之地封给了晋文公,阳樊人意志刚烈,宁死不屈,以战车列卫相依,当作屏障,继而筑土为城。《风雨故城思轵国》,写到晋文公民主开明,保全了众志成城的集体尊严,成就了一个历史上享有很高人文地位且富冠海内的诸侯小国。灰黑的夯土层,遍布的夯窝,裸露的或生或腐或粗或细的根系……永刚顺着时间长河的道道涟漪,去打捞古轵国衰落的历史,叙述中显出文字的沉郁。
作为儒学思想的后期集大成者,朱熹在武夷山生活、著述、教学达50余年,使武夷山成为朱子理学的摇篮和宋、元、明三朝理学驻足之薮,为武夷山沉淀下不菲的人文价值。《武夷山中访朱熹》,既写出了武夷山的秀美,也写出了朱熹理学的深厚。
永刚还去了汶川地震的重灾区遗址,在《那洁白的小花》中,他写到了惨烈与痛悼,也写到了坚毅与信念,他逢到一位30岁左右的羌族女人,女人在废墟旁开了一家出售鲜花香烛等祭祀用品的商店,木质的小木屋有点简易,雕着民族风味的图腾。作为地震的幸存者,女人重组了家庭,跟了一个带着小女儿的大巴司机。永刚从交谈中有了感慨:他们埋葬了自己的亲人,流干了眼泪,无论如何,生活还得继续,直面现实,珍惜生命,有尊严地活着,就是对长眠故人的最大告慰。在文章的开篇有这样的描写:“纤细的长茎托起耀眼的嫩白,柔韧的叶片随风摇曳,在春的静绿中,在钢筋混凝土的残垣断壁间,这朵小花盛开得出类拔萃。”读完整篇文章,回想这段文字,觉出情味绵长的意绪。
五
语言是一个作家的能力。一个作家能不能走得远,完全取决于这种能力的强弱。当然要有积累,生活的积累,操练的积累,阅读的积累,包括文学的审美取向,对语言的理解及敏感程度。永刚的语言透显出他的气质与睿智,透显出他的人生经验及对语言的把握,如果没有对汉语语言的灵动感知,不可能有如此的落笔:
“苦难磨炼勤劳者的意志,毁灭懒散人的心智。惰性就像一把锁,锁住了视野,禁锢了创造力。现实中,遭遇厄运,绝不意味着没有希望,看不到明天。看似荒芜的境地,其实孕育着鲜艳的梦想之花。纵然世事百变,命运多艰,只要勤劳,只要不在失望和懒散中自暴自弃,就有可能让梦想之花在绝境里怒放,把贫困变成通向幸福的桥梁。”(《密林深处的农家小院》)
“一年四季,春最不寂寞,因为有花,且是初始之蕊。此时之花,如同小儿,有着惹人怜爱的生命,一天天,花非花。那种一日一芬芳的花容,牵挂、陶醉了多少怦然而动的心扉。”(《春观花开》)
“冬雪拉长了白昼的体量。雪天,只要雪未消融,夜,便不再属于暗色系。即便是子夜,也有着黎明的影子。寂寂深夜,雪沙沙,掀起一帘幽梦。”(《雪痕》)
不少文章里,都会时不时闪现个性的警句,哪怕是小感小悟,也感得哲理,悟得精辟:“文化遗址是一个文明不会腐朽的档案。”(《不朽的文明档案》)、“村庄是人的家园,更是树的故居。”(《乡村的年轮》)、“风是微薄的肌肤,传递着夜的温度。”(《乡村的表情》)、“沉静是一种极致的美。”(《远山》)、“鸟,是花中之花。”(《春观花开》)、“山水田园间,蕴藏着令人向往的幸福密码。”(《乡野镜像》)、“碌碡是麦场的名片,麦场是乡村的名片。”(《拉碌碡的老人》)、“粗陋而憨厚的乡戏,永远飘浮在单纯的童年里。”(《乡戏》)
这些句子即如乡间小路上的野菊,本来蜿蜒的阡陌就意味隽永,却这里那里乍然发出野艳与水灵,更是让人眼睛明亮、内心清爽。
有一部分作品,是散文诗样的写作。散文诗具有散文的外形,诗歌的内质。永刚为了适应某些题材和情感,以及适应某种表达,而采用了散文诗的形式。比如《六月》,六月是火热的季节,是农民表演的黄金时段。为了展示对六月的理解与抒发,永刚连续以“六月”提领,江河排浪般突出了“热似火,烈如焰”的铺展在大地上的六月。另外,报告文学作品的加入,拓展了集子的叙事空间,让集子多了几分厚重。
好了,絮絮叨叨已说了不少,该收尾了。我始终认为,散文的格局越来越宽泛,写作也越来越自由,没有一个严格的说法,要求必须怎样,必须不能怎样,只要你写的文章能够感染人,就可以肯定并且值得坚持。而且,越朴实、越自然、越纯真的东西就越有生命力。永刚的散文,实属随性的纯然的且又是自觉的写作。永刚曾经有一部《那山·那水·那人》,现在又有了《乡村的年轮》,可见是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着,只要坚定一个方向,善于学习,善于发现,善于纠正,就必然会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开满鲜花的远途。
(王剑冰,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河南省散文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