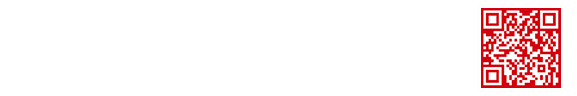大学毕业后,我到一家专业报做编辑,按部就班地领着一份微薄的薪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倘若没有朋友来,平日里饮食总是因陋就简,万万不敢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而拥有自己的房子,更是海市蜃楼般遥不可及的梦想。
一天晚上下班后,我发现临街的出租房楼下,多了一家可以移动的小吃摊。摊主是一对温和的中年夫妇,穿着朴素而干净。我信步走到小吃摊跟前时,汉子分明吓了一跳——他还没有学会招揽顾客,一脸的不尴不尬似笑非笑。
我问摊主卖什么吃食,汉子拿眼睛盯了女人一眼,女人马上大声说:“我们主要卖云吞和水饺。”长居中原,很少接触粤语,我完全没有“云吞”这个概念。看我一脸疑惑,汉子憨憨地笑了:“‘云吞’是馄饨的另一种叫法。”
我要了一碗馄饨,女人手脚麻利地开始忙活,汉子则木木地立在一边。馄饨很快就出锅了,瓷碗里晶莹剔透的面皮中隐隐地透出一抹粉红,牛骨、虾皮熬成的汤底让人垂涎不已。
我吃完馄饨抬起头来,却意外地发现汉子正就着路边微弱的灯光读一本书。同是天涯沦落人,我的心底不自觉泛起一丝温暖。我记得书橱里还有几本金庸和张恨水的小说,便想改天拿来送给汉子。就在掏出钱包准备买单的一瞬间,我突然呆住了——汉子正在阅读的那本书,并非我想象中的武侠或者言情小说;我仔细地看了一眼书的封面,书名叫《灵魂只能独行》,学者周国平先生的哲思随笔集。
从这天起,我晚上下班后偶尔去吃夜市,总是先拐回住处,径直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下楼。这个都市村庄地处城乡接合部,位置有点儿偏僻,清冷的大街上人迹寥寥,汉子的生意总是有一搭没一搭的。我每次将书递过去的时候,汉子总是酡红着脸,仿佛不胜酒力一般。吃罢馄饨,我带着汉子看完的上一本书上楼,心里总是弥漫着淡淡的欣喜。我是个爱书的人,看到这个每天和面粉、饺子馅厮混在一起的粗笨汉子,居然能够把书保护得这么好,我不由得对他充满了敬意。
时间长了便慢慢得知,摊主夫妇都是本市的下岗职工,下岗前他们在同一家国营单位上班,那家单位丰厚的税收曾经是这座城市的经济支柱。汉子下岗前,是单位的宣传干事,经常要写写材料出出墙报什么的。我终于找到汉子喜欢读书的根源了,我甚至觉得,他应该有一个更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读书人卖馄饨,多少有点儿牛鼎烹鸡、明珠弹雀的意味。
时光一如这座城市的金水河,总是懒洋洋的。如果你不加留意,甚至感觉不到它的流淌。
数月后的一个晚上,我正坐在一张小桌旁吃馄饨,忽然听见有人大喊一声:“谁让你们在这里摆摊的?!”
从一辆市政执法车上下来三个人,他们一起朝汉子的摊位走来。汉子惊慌地站起身来,不知怎么连带着把案板掀翻了,一时间面粉、饺子馅、佐料、青菜等散落了一地。那三人见此情形,脸上似乎有些不自在,其中两人上前扶起了案板。三人转身上了车,车子启动前,开车的年轻人探出头冲汉子说:“以后不要在这里摆摊了。”
我蹲下身子,帮助汉子清理残局,把还能用的物料一一捡起来。自始至终,我们都没有说一句话。也许是深重的夜色掩护,也许是汉子早已习惯了生活的严酷——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甚至连一句抱怨的话都没有。
第二天晚上下班后,遍寻不见那对夫妇的馄饨小吃摊,他们就像低到尘埃里的一滴水,倏忽之间蒸发了。
此后多年,只要晚上去吃夜市,我就会莫名地想起那对夫妇来。不知道他们后来安身何处,在这座灯火辉煌的繁华都市,他们是不是在某一个清冷的角落又撑起了一方天地?他们的小吃摊,是不是依旧生意清淡?……我一遍遍地想起那个低头垂目的汉子,想起他每次从我手里接过书的那一刻,满脸酡红的窘迫不安和由衷欢喜。我几乎有点儿思念他们,犹如思念自己远在故乡的亲人。而那对夫妇,我再也无缘相见,他们仿佛彻底地从这座城市消失了。
时光一点点打磨掉过去的记忆。有一段时间,我甚至觉得自己不再记得他们了。假如那天晚上领导不安排我加班,假如我深夜回到家不随手打开电视,假如我不是正好调出了本市的这个频道而是其他频道,我想自己是真的要把他们完全忘记了。
那是重播的一档新闻节目: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有几个惯偷到一处正在施工的工地上盗窃建筑材料,刚好被一位工友发现了,他奋不顾身地冲上去阻止。惨祸就这样发生了,为了逃脱罪责,有人在黑暗中狠狠地刺了他一刀,然后四散逃去。就是这势大力沉的一刀,锋利地隔断了这位工友与尘世的联系,使他和自己的妻子儿女永远阴阳两隔。
记者的镜头长时间定格在这位工友的面庞上。我知道,记者是想让市民记住中年汉子这张憨憨的面孔——因为从这一刻起,这座城市授予了他“见义勇为英雄”称号。
我在黑暗里一下子跳将起来——这张脸如此熟悉,如此安详和沉静。多年前,他曾经摆过一个毫不起眼的小吃摊,就在我租房的楼下。这么多年来,他一直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低处,可是,他的灵魂,在这一天却展翅飞上高空,被云吞去了。
二十多年来,我再也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云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