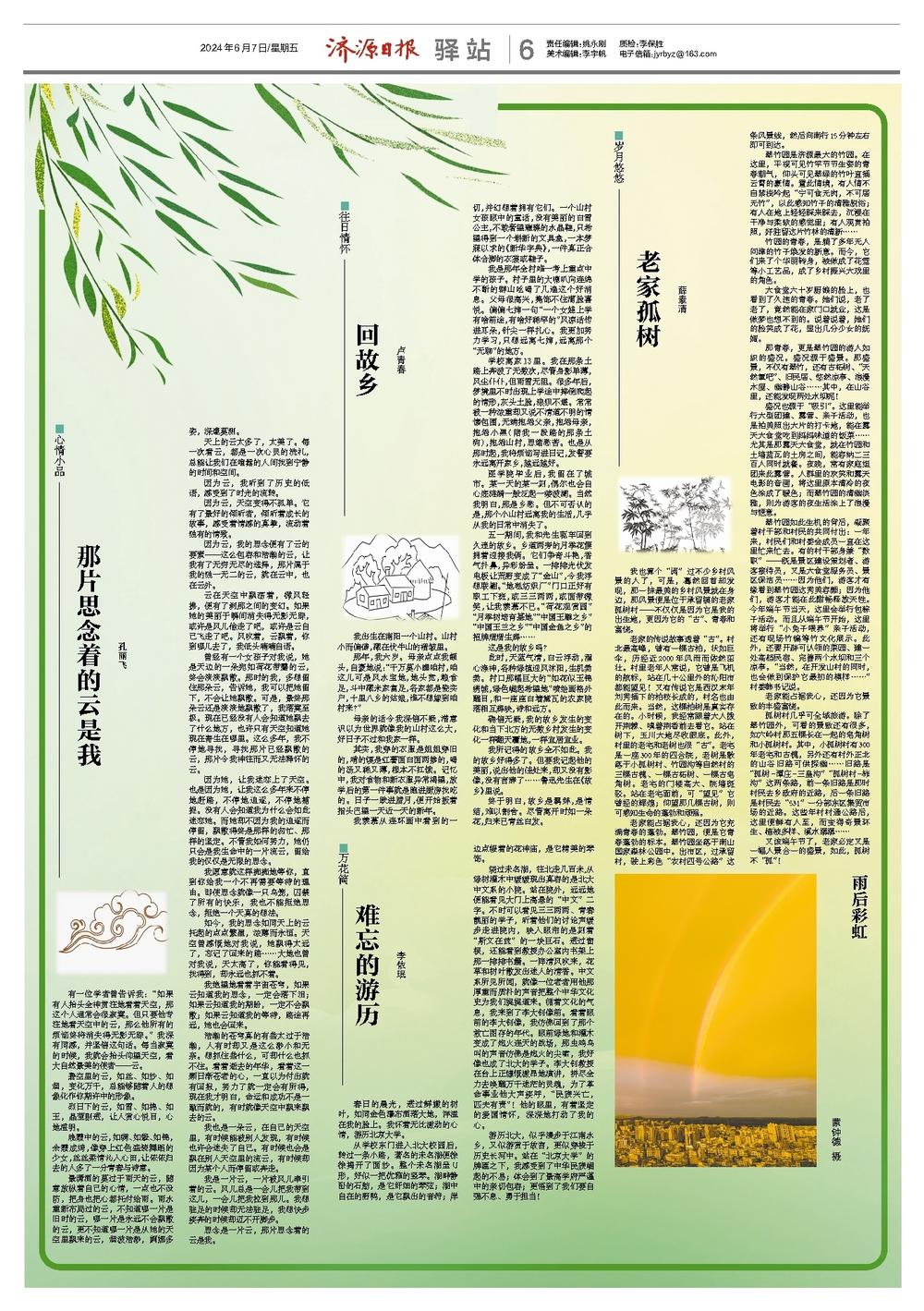我出生在南阳一个山村。山村小而偏僻,藏在伏牛山的褶皱里。
那年,我六岁。母亲点点我额头,自豪地说:“千万莫小瞧咱村,咱这儿可是风水宝地,地头宽,粮食足,斗中藏米家富足,各家都是瓷实户,十里八乡的姑娘,谁不想嫁到咱村来?”
母亲的话令我深信不疑,潜意识以为世界就像我的山村这么大,好日子不过和我家一样。
其实,我穿的衣服是姐姐穿旧的,啃的馍是红薯面白面两掺的,喝的汤又稀又薄,根本不扛饿。记忆中,我对食物和新衣服异常渴望,放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跑进厨房找吃的。日子一跌进腊月,便开始扳着指头巴望一天近一天的新年。
我羡慕从连环画中看到的一切,并幻想着拥有它们。一个山村女孩眼中的童话,没有美丽的白雪公主,不敢奢望璀璨的水晶鞋,只希望得到一个崭新的文具盒,一本梦寐以求的《新华字典》,一件真正合体合脚的衣裳或鞋子。
我是那年全村唯一考上重点中学的孩子。村子里的大喇叭向连绵不断的群山吆喝了几遍这个好消息。父母很高兴,掩饰不住满脸喜悦。偏偏七婶一句“一个女娃上学有啥前途,有啥好稀罕的”风凉话传进耳朵,针尖一样扎心。我更加努力学习,只想远离七婶,远离那个“无聊”的地方。
学校离家13里。我在那条土路上奔波了无数次,尽管身影单薄,风尘仆仆,但雨雪无阻。很多年后,梦境里不时出现上学途中摔倒爬起的情形,灰头土脸,狼狈不堪。常常被一种浓重却又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包围,无端抱怨父亲,抱怨母亲,抱怨小黑(陪我一段路的那条土狗),抱怨山村,思绪愁苦。也是从那时起,我将烦恼写进日记,发誓要永远离开家乡,越远越好。
医学院毕业后,我留在了城市。某一天的某一刻,偶尔也会自心底涟漪一般泛起一缕波澜。当然我明白,那是乡愁。但不可否认的是,那个小山村远离我的生活,几乎从我的日常中消失了。
五一期间,我和先生驱车回到久违的故乡。乡道两旁的月季花簇拥着迎接我俩。它们争奇斗艳,香气扑鼻,异彩纷呈。一排排光伏发电板让荒野变成了“金山”,令我浮想联翩。“地毯纺织厂”门口正好有职工下班,或三三两两,或面带微笑,让我羡慕不已。“荷花观赏园”“月季树培育基地”“中国玉雕之乡”“中国玉兰之乡”“中国金鱼之乡”的招牌熠熠生辉……
这是我的故乡吗?
此时,天蓝气清,白云浮动,濯心涤神,各种绿植迎风沐阳,生机勃勃。村口那幅巨大的“如花似玉锦绣城,绿色崛起希望地”喷绘画格外醒目,和一座座白墙黛瓦的农家院落相互辉映,诗和远方。
确信无疑,我的故乡发生的变化和当下北方的无数乡村发生的变化一样翻天覆地,一样宜居宜业。
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但要我记起他的美丽,说出他的佳处来,却又没有影像,没有言辞了……鲁迅先生在《故乡》里说。
终于明白,故乡是羁绊,是情结,难以割舍。尽管离开时如一朵花,归来已青丝白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