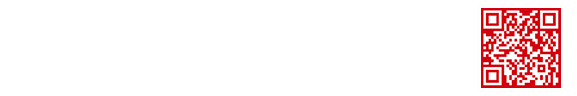谷雨,园区的梅林,巧遇赏梅旧友。痴情的样子,得意忘形,专注地旁若无人。走到近前,还有不知。轻呼两声,才似醒来的样子。
见是故人,只应一下。转身,依然专情地摆弄着相机中的梅花。透过清亮的镜头,可见浓重的红梅,耀眼地闪亮。一直听梅诗、梅歌、梅赞,却没有近距离接触过这红得发紫的梅花。梅,花朵不大,一如点点,那花萼是深红色,又像是褐红色。三层花瓣儿之下,是细长的花蕊。花蕊的毛,柔细,也是古铜色。不过,花蕊的柔毛,很挺拔,直直地,顶端是圆且浓的红头,顶上有冒烟的感觉。
友人是弄梅高手,半生爱梅,尝言梅是情至所爱,无怨无悔。他一边拍梅,一边品梅。他说:“你看,这梅花,没有一朵是昂着头长,大多是低着头或平视着生长,无论怒放还是尚在蕾苞,抑或欲放不能,都显示着自身的高贵而不张扬,纯粹而不避朴实。”
真的,所能看到的是,一棵树上,竟然没有一朵梅花是骄纵地向着天空。
真奇了,怪了。
友人是林业专家。据说,济源的梅花是他引进来的。据说,园区中的梅花,也是他引进并栽植其间。猜想,可能如此,他对这里的梅,有一种天性的爱。
天,有点阴,却没有要下雨的意思。梅花,也非文人或情感深重的人笔端湿漉漉的样子,甚至有点干涩。雍容,肥臾中,那梅红,红得发乌,红得浓重,红得似乎就像一颗颗滚烫的红宝石,沉甸甸地挂在枝头。
也曾爱梅。
记忆里,永远是清趣园那藏在树丛中的黄梅。黄梅花开放得早,每年的十二月份儿,就显示出貌不惊人的神态了。早些年,多雪,雪地里只留下一个人的两行脚印。围着湖畔石径,欣赏着荷花残枝的枯美,转入幽径,便是三两株黄梅。那梅,是活生生的会动。早晨起来的时候,一枝苞头,花瓣把花蕊包裹得严严实实。雪季,无论太阳出不出来,午时前后,黄梅都要将花瓣儿张开。走到跟前,她会口吐芳香,将鼻息中的所有味道冲扫而去,留下醉神的香。傍晚,顶着飘扬的落雪花,你再到这里看梅,发现这花瓣儿,又将花蕊严严实实地封闭起来。
大自然真神,大自然也有她通灵的神秘。
悠悠荡荡地走开,真的不舍离去。当转身闲庭园区北楼后边的巷道,那一排红得发紫的梅树,挂满了一串串的梅花苞。所有的梅没有放开,而树,却色泽浓烈地透出一种凝重的古香。这梅花夺人的不是其喷出的香,而是挂在半空中的红珠子,弥漫了整个园林。这珠子并不是人所常见的能够闪烁出光焰,更没有相机镜头里透亮的色泽,而是一种深红、铁红、黑红,红得让人透不过气来,红得让人看不到任何亮度的巨红。
穿径轻过,不敢重步,生怕惊得她醒了,只想让她静静地休养,待日艳阳来时,红梅一发怒开。
归来,一路低头无语,思却几多梅诗吟唱,从不知其梅之色彩浓红这当。这,可能是文人重了情思,忘了真挚。哎,真正的梅,这等点点紫红,似重珠,击人心肺,伤人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