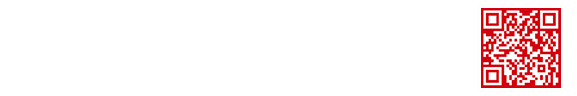“西瓜,又绵又甜的西瓜……”,酷夏在街头的西瓜叫卖声中拉开清凉,我的思绪却飞到记忆中那片绿油油的瓜地。圆爷的西瓜地盘踞在心灵深处,成为童年岁月的固有记忆。
这片瓜地在老家山崖边一片倾斜的土坡上。其时,圆爷60多岁,高个子,赤红脸,声若村头挂着的洪钟。圆爷为人豪爽,是村里的老队长,加上辈分大,村里30多个半大孩子都亲切称他圆爷。山村夏天酷热难耐,去水坑洗澡,大人们看得紧不让去,去山沟堰头边摘野果,次数一多也感无趣,圆爷的瓜地就成了伙伴们心心念念的地方。这块地原是一大片荒草坡,只有下面二分多是耕地,其余全是红土,因此得名“红土坡”。某天圆爷在地里干完活儿,对老伴说,把这荒坡收拾一下,种点西瓜。老伴阻止说,净是料礓堆,种啥也不长。圆爷说干就干,光料礓拉了二三十平车,半坡处不能用牛犁地,他就用头刨种。
圆爷整好地后,开始种西瓜。从春天点种开始,侍弄秧苗,拔草,施肥,圆爷每天待在瓜田,饭也由家人送到地头。圆爷悉心照顾着每个瓜,拍拍这个,摸摸那个。他看待这些瓜就像自己的孩子,日夜守在瓜地。
“碧蔓凌霜卧软沙,年来处处食西瓜。”一有空,我们就来到瓜地边,散落田间的西瓜和甜瓜在山风的吹拂下时隐时现,摇曳着每个人的心。我们时而瞄着那片绿莹莹的瓜地,时而望着连绵起伏的山崖,庄稼在烈日下晒得蔫巴巴的,散着闷热的气息。圆爷头戴草帽,短褂敞开,裤脚高高卷起,拔一下草,抹一把汗,咳嗽几声。伸腰时,看见坡上面一双双渴巴巴的眼睛,圆爷招呼道:“来,给你们吃点瓜。”说着,他摘一个半大的瓜,“咔嚓”在板上切开,汁水四溢。孩子们从草坡上冲下来,接过圆爷递来的一片薄薄的西瓜。西瓜的清凉在我们长久的焦渴等待中直冲喉咙,甜到心底,每个人都笑咧了嘴!
瓜地中间隆起一道梁,瓜棚搭建在西北角,西南角靠近一片荆棘处,于我们而言就有机可乘。总不能一直等着圆爷赏瓜吃,小孩子们深谙此道,有伙伴们想出高招,密谋一番之后,于是依计行事。有人去瓜棚和圆爷扯话,这个说:“我妈让我来问问用麦换瓜咋换?”那个说:“我奶说拿玉米换行不行?”还有的缠着圆爷:“爷,讲个故事呗。”乱哄哄之际,有人趁机溜进瓜地,顺藤摸上几个瓜。又一次去,话侃到一半,圆爷出棚拿地边的草帽,正看见两三个孩子慌慌张张摘瓜。“又来了,小兔崽子们,看我不打断你们的腿!”圆爷一声大吼,吓得有人扔掉手中的瓜,往荆棘丛里藏。转身时,瓜棚里的几个人也跑了。“小兔崽子们,再来我非打断你们的腿不可!”圆爷对着坡上狂跑的背影大喊。孩子们在怒骂声中嘻嘻哈哈跑开了。
种瓜人的日子有甜蜜也有心酸。正值瓜果生长期,老天突然下了冰雹,圆爷的瓜地遭了秧,满地的瓜果被冰雹砸得一片狼藉。圆爷把半生半熟的西瓜甜瓜拉了几大平车。那天我刚放学,妈妈支使我去南洼圆爷家拿瓜。等我赶去时,迎面碰见几个伙伴或夹或拿着大大小小的瓜。能多拿都多拿点,圆爷看着满车生瓜唉声叹气。我一手一个,怀里又搂了俩甜瓜回去。西瓜切开后,泛着白瓤,透点微红,再长十天半月就成熟了,可惜一场冰雹把圆爷半年心血打了个空。妈妈把生西瓜切成窄窄条块,炒了一大锅,清香泛甜,光滑脆溜,配着玉米糁很是下饭。那几天,村里家家户户吃着炒西瓜。在我们大尝其鲜的同时,背后是圆爷的心痛和无奈。有时候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世上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内心的痛苦只能圆爷一个人去承担。
几年后,圆爷嫌那块瓜地收成不好,移到九亩地,这里平坦开阔,土地肥沃,正是良田。东西望去一览无余,就是落地一只麻雀也能看得清清楚楚。我们这些孩子就像圆爷赶也赶不走的麻雀,早上来,午后来,傍晚还来。有次西瓜切开竟是黄瓤,同样清甜可口,众人皆感惊奇,那是我第一次吃到黄瓤西瓜。
西瓜大量成熟时,圆爷会让圆奶去看瓜。他和儿子拉一平车西瓜甜瓜走村串巷卖瓜。那时,人们大多用麦子换瓜,一斤麦一斤瓜,大人们一掂量,一斤麦子磨成面配点菜够两三个人吃。总不能贪吃几口瓜,缺了一家人的口粮。种地人总是在尝鲜和填口粮之间快速作出抉择。所以,任你吆喝半天,只有几户人家来换,有哭着想吃瓜的孩子硬被家人哄回。如果一斤麦能换成两斤或两斤半瓜,就会多几家去换。碰上熟人朋友或亲戚,就会折损几十斤瓜。
后来,圆爷从有病到去世两年里,再没有种过瓜。圆爷的瓜地成了大家饭后念念不忘的谈资。如今,西瓜年年有,可是少了当初的甜蜜和惬意。当初的我们,站在山间地头,顶着烈日,吃着西瓜,说笑声随着山风在田野里飘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