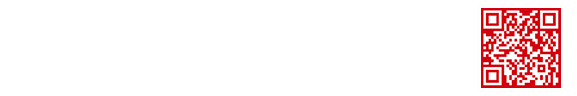姥爷今年100岁,姥姥95岁,两位老人相扶相携,从北京到河南,辗转千里,陪伴一生。姥爷有点耳背,姥姥轻度糖尿病。两位老人目前生活基本自理,身体各方面都挺好。姥爷稍显唠叨,姥姥思路清晰,经常提醒姥爷。尤其是家庭聚会时,姥爷说起来没个完,谁劝也不听,只有姥姥劝得住。无须誓言,没有山盟,两位老人一路相伴的时光,或许就湮没在这些絮絮叨叨的烟火中,平凡相守,温暖从容。
相遇陶然亭
姥爷14岁就离家外出求学,先是到洛阳,然后到开封,最后在北京上大学。上大学时,姥姥的父亲是姥爷的老师,姥爷因之与姥姥相识,两个人的初次相遇就在陶然亭中。
陶然亭的清风或许无意,但依然吹皱了两个人彼时的心湖,刹那芳华,终成一生的承诺。两个人不仅有年龄上的差距,还有地域身份上的差距。姥姥成长于北京书香之家,还是家中受宠的老幺;姥爷则是来自河南乡下的穷小伙,可以想象两个人当时面临的压力。父母家人终究抵不过年轻人的决心,两个人在北京举行了婚礼。听姥爷说,当时办的是西式婚礼,新郎新娘交换的戒指还是姥爷借钱买的。我在姥爷家见过两位老人的结婚照:姥爷西装革履打着领结,梳着三七分背头;姥姥一袭白婚纱,披着大波浪烫发,头上戴着花环,与如今年轻人的婚纱照一般无二,反而更有一种复古的韵味。
婚后,他们在北京临时安了家,大姨就在北京出生,取名燕萍,以纪念在北京出生的第一个孩子。1年后,姥爷因乡情难舍,张罗着要回河南老家。姥姥自然不愿离开从小生活的北京,但没能拗过姥爷,两个人还是带着孩子回了老家。
结庐杏林旁
回到老家,一切从零开始。尤其是姥姥,一个北京长大的姑娘,来到河南济源,各种不适应——方言听不懂,农活啥都不会干。母亲和舅舅出生后,姥姥带着几个孩子,努力适应生活。那时做饭烧散煤,需要和煤填炉灶,姥姥甚至连个铁锹都拿不好。姥爷的弟兄几个也都成了家,几大家子挤住在一个院子里,艰难可想而知。当然,姥姥从来没有说过这些,我是后来听母亲说的。
20世纪60年代,姥爷到思礼镇荆王村做了乡村医生。后来,在荆王村盖了房子,一家人才算安定下来。我儿时关于姥姥家的记忆,始终伴着消毒水和紫药水的味道。
姥爷在大队部的房子里行医。在我的记忆中,每天早上姥姥家起床后的第一件事,不是做早饭,而是蒸针。那时,一次性的注射器、输液管等医疗器械非常罕见。早上第一件事就是给注射器、针头、输液管消毒,放在蒸锅上蒸,供一天使用。医疗器械全部消毒完后,才轮到做早饭。
20世纪90年代,姥爷家翻盖了两层小楼,门口的平房被建成了医疗所。姥爷这才从大队部搬回家,继续给乡邻看病。姥爷行医的原则是决不让病人多花冤枉钱,总是用最便宜的药,往往药到病除。
姥爷给人看病,一看就是一辈子,直到90岁那年,在家人的一再劝说下,才勉强同意歇业。但是,仍然有村里的老人,遇到小病痛过来找姥爷,有时不为看病,就是说说话。姥爷俨然成了心理医生,为村里的老人纾解忧烦。一位老大夫说的话,自然在心理上还是管用得多。
姥姥一辈子操持家务,抚养6个孩子成人。我小学、初中的寒暑假都是在姥姥家度过的。印象中,两位老人几乎没有红过脸。只有一次,因为儿女的婚事,两个人生气闹别扭,意见分歧很大,姥姥气得把一案板切好的菜扬撒了一地。姨妈当时在北京工作,姥姥希望姨妈在北京成个家,姥爷非让姨妈回来。最终,还是姥姥让了步,姨妈在济源成了家。用姥爷的话说,姊妹们要相互有个照应。
养生三餐饭
姥爷有胃病,60岁那年大吐血,从那以后为了养胃,一直没敢吃肉,吃的都是好消化的汤饭。为了保证营养,姥爷从60岁开始,和姥姥每天坚持喝牛奶,一直到现在。91岁那年,姥爷做了胃镜检查,医生对姥爷说,没发现异常,可以放心吃肉了。姥爷这才重新开始吃肉,也是从那年开始,两位老人基本形成了固定的一日三餐。我曾经问过一位专业人士,老人的三餐是否营养,答复是不但营养而且养生。
姥爷一般6点左右起床,起床后开始扫院子,收垃圾,慢慢规整院子里的花草、物件等。待到院子都收拾停当后,他才打开电视,看新闻,因为耳背,音量调得很大。然后,他看报纸,《参考消息》订了一辈子,现在每天还在看。姥姥起得迟。
8点多,两位老人开始吃早餐。早餐是鸡蛋甜汤,每人三个鸡蛋——两个荷包蛋,一个蛋花。早餐配菜只有两种,清炒瓜片或土豆丝。上午10点多,每人喝一盒热牛奶。午饭是炖鸡腿,汤里炖上山药、红萝卜、大枣。每人一个鸡腿,姥姥配一个馒头,姥爷有时就喝一碗鸡腿汤,馒头也不吃。晚餐是雷打不动的手工馄饨。瘦肉和葱花调馅,手工和面,擀成薄薄的面皮,每人一碗酸汤馄饨。下午有时会加点时令水果,一日三餐基本不变,一直持续将近10年。
姥爷快过100岁生日了。那天,大家聚在一起商量怎么庆祝,姥爷忽然对大姨说:“再过几年,你们年纪也大了,伺候不了我们了。到时候,我伺候你妈。”大姨今年已经73岁了。姥爷说这话时,怕是不知道自己多大了。他以为自己还年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