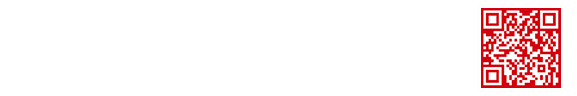小外甥就要去上班了,这两天暂住在我家里。看着他日渐懂事,我欣慰之余,又湿润了眼眶。
小外甥比我家妞小半岁,小时候,总是跟在我身后,一遍又一遍地喊:“小姨,小姨……”两三岁光景,黑黑的,瘦瘦的,眉间有一颗痣。他整天笑眯眯的,小嘴像抹了蜂蜜般,甜甜的,真是讨人欢喜。有一年暑假,我领着妞,在姐姐家小住。他便常常跟着我,小姨长小姨短地喊。有一次,姐和姐夫去地里干活儿,把他托付给我照看。一不留神,妞就把他的脸抓破了。他也不哭,而我却很内疚。他虽是男孩子,但个头小,又瘦,根本不是妞的对手。可是,他不记仇,还是冲着妞喊“姐姐”,我的心都被他萌化了。
姐夫甚是宠爱这个幺儿子,给他起了个小名——黑瓜。他常常“黑瓜黑瓜”叫个不停,多少怜爱在里头,大家只要听听他的喊声就知。这孩子黑瘦黑瘦的,或许这就是这个昵称的由来吧!每个热爱孩子的父母,心里都埋藏着一个小名吧,关于孩子的别称,我想。日月如梭,岁月更迭,那个小不点儿,转眼已18岁了。去年秋天,他踏上列车,远离家乡,上了大学。他在父母的呵护下应声长大。他无忧无虑、天真可爱,而这一切,也在去年冬天姐夫去世后戛然而止。有些苦难是悄悄来临的,有些长大是没有声息的。
转眼又过了一年,他19岁了.像他这般大的孩子,放了暑假,许多就在家里“躺平”。而我的小外甥,却开始考虑,如何赚取生活费。这不是他该思虑的事,在去年冬天之前,他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孩子。自从姐夫出了车祸猝然去世后,这个孩子仿佛一夜之间长大成人了。我既欣慰,又感伤,不能自已。他在富士康找了工作,明天就要去干活儿了。这两天得体检、办卡,复印一些证件。而我作为小姨,却帮不上任何忙。
去年姐夫出事,瞒了他一个月——小外甥刚读大一。临近春节,他就要回来了,我们把谎话圆了又圆,怕漏了破绽。该怎么告诉他呢?我们也是过了好久,才慢慢接受了这个事实。而我的小外甥,还是个孩子,能接受这命运的暴击吗?回来前一天晚上,我与他通了电话,他还是兴高采烈,而我佯装与他一样。第二天,我与家人出门办事,事还未办完,电话就响起来,是嫂子打来的。她刚把小外甥接回家,就“东窗事发”了,那么迅疾,来不及思量。“你们快过来吧,我顶不住了,他闹腾得厉害!”嫂子在电话里连声地催。我们急匆匆过去,屋子里静悄悄的。“刚才,他还大喊大叫,谁劝也没用。”嫂子低声说,“现在,他又把自己关在卧室里,谁喊也不理。”我们拧开卧室的门,走了进去。他面对着窗户站着,傻了似的。他还是瘦小,单薄的身子,依旧弱不禁风。我们陪着他干坐着。究竟说什么好呢?我搜索枯肠。那些饱含热泪的话,不说也罢!下午时分,我陪他去人民医院做核酸检测,在等待的过程中,他浑身颤抖不已。“你冷吗?”我问。他摇摇头。他哭一声也好呀,他倔强得让人心痛。
“他在学校找了一份兼职。”姐姐在电话里对我说。“兼职?”我愕然。“是呀,他在学校里帮餐厅洗碗,中午可免费吃一份午餐……”姐姐在电话里断断续续地说。这是今年春天的事。“这孩儿长大了,知道心疼母亲了!”我说。鼻子一酸,想哭,那一刻。“是呀,供他上学的钱还是有的,可是他……”姐姐哽咽了一下继续说,而我的思绪却飘得好远。
“他硬要去昆山打工,我该怎么劝呀?票已经买好了。”五月下旬,姐姐又给我打电话。“这是好事,让他去吧。”我说。“可是昆山和上海距离很近,那儿疫情严重,去不得呀……”姐姐满腹忧虑。可不是嘛,那时,上海疫情确实严重。听姐姐如此一说,我也开始顾虑重重。“闲了,我好好劝劝他。”我说。姐姐还要说下去,手机突然断电关机了。姐姐软硬兼施,到底让他把票退了,这是后来的事。我还未来得及给小外甥打电话,姐姐就向我报告了好消息。也好,也不是真过不去,非得他挣钱不可。他懂事得让人泪目。
他到底找下了活儿,回来济源不久。“不能和去昆山比,学费是挣不了了,生活费或许可以挣到。”这是小外甥的原话。他就要出门工作了,这两天借住在我家里。看着他忙得脚不沾地,我有些欣慰,又有些伤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