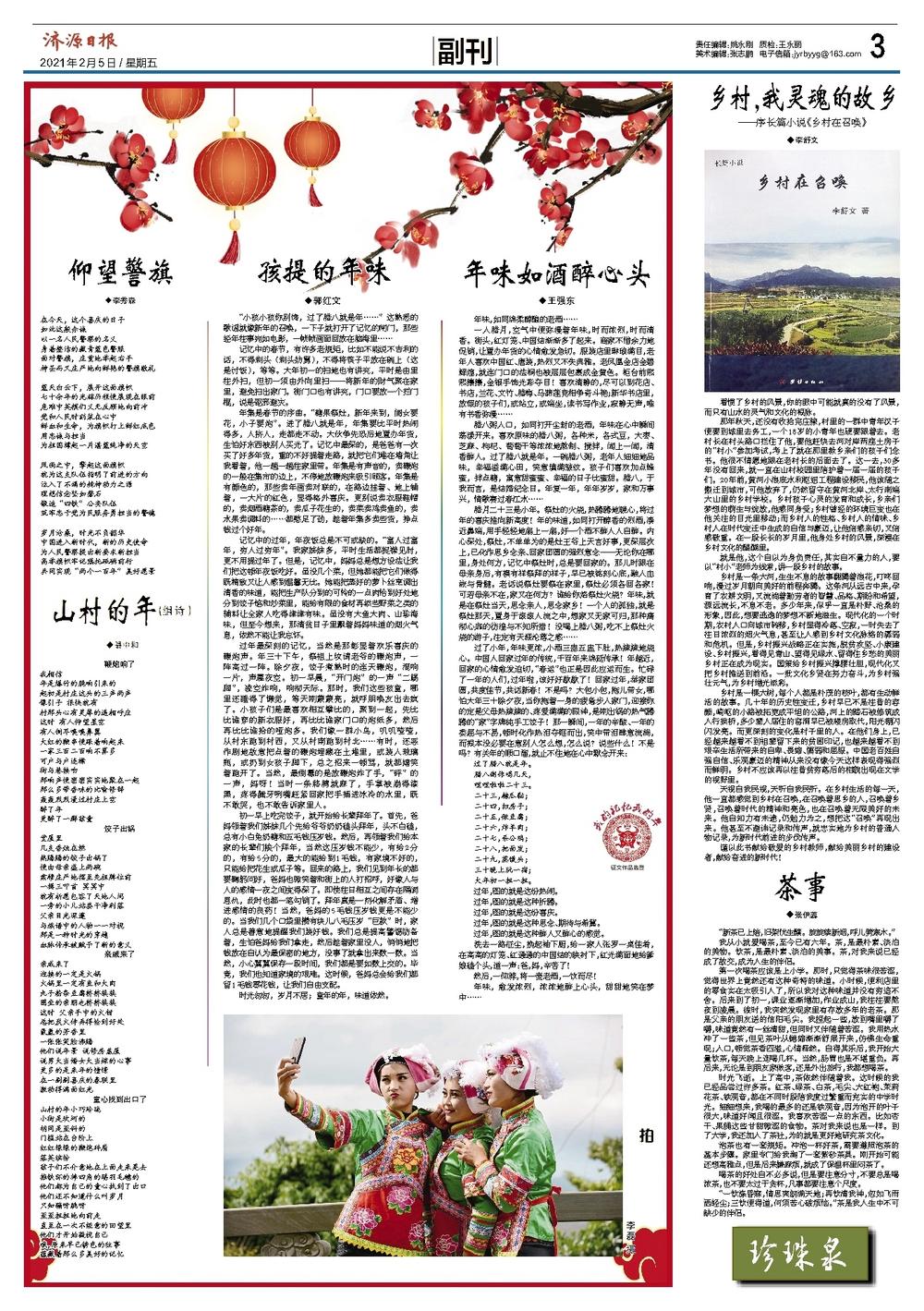“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这熟悉的歌谣就像新年的召唤,一下子就打开了记忆的闸门,那些经年往事宛如电影,一帧帧画面回放在脑海里……
记忆中的春节,有许多老规矩,比如不能说不吉利的话,不得剃头(剃头妨舅),不得将筷子平放在碗上(这是讨饭),等等。大年初一的扫地也有讲究,平时是由里往外扫,但初一须由外向里扫——将新年的财气聚在家里,避免扫出家门。街门口也有讲究,门口要放一个拦门棍,说是驱邪避灾。
年集是春节的序曲。“糖果祭灶,新年来到,闺女要花,小子要炮”。进了腊八就是年,年集要比平时热闹得多,人挤人,走都走不动。大伙争先恐后地置办年货,生怕好东西被别人买光了。记忆中最深的,是爸爸有一次买了好多年货,重的不好提着走路,就把它们堆在墙角让我看着,他一趟一趟往家里带。年集是有声音的,卖鞭炮的一般在集市的边上,不停地放鞭炮来吸引顾客。年集是有颜色的,那些卖年画卖对联的,在路边挂着、地上铺着,一大片的红色,显得格外喜庆。更别说卖衣服鞋帽的,卖烟酒糖茶的,卖瓜子花生的,卖菜卖鸡卖鱼的,卖水果卖调料的……都憋足了劲,趁着年集多卖些货,挣点钱过个好年。
记忆中的过年,年夜饭总是不可或缺的。“富人过富年,穷人过穷年”。我家姊妹多,平时生活都捉襟见肘,更不用提过年了。但是,记忆中,妈妈总是想方设法让我们把这顿年夜饭吃好。虽没几个菜,但她都能把它们做得既精致又让人感到温馨无比。她能把蒸好的萝卜丝烹调出清香的味道,能把生产队分到的可怜的一点肉恰到好处地分到饺子馅和炒菜里,能给有限的食材再添些野菜之类的辅料让全家人吃得津津有味。虽没有大鱼大肉、山珍海味,但至今想来,那清贫日子里飘着妈妈味道的烟火气息,依然不能让我忘怀。
过年最深刻的记忆,当然是那彰显着欢乐喜庆的鞭炮声。年三十下午,祭祖上坟请老爷的鞭炮声,一阵高过一阵。除夕夜,饺子煮熟时的连天鞭炮,混响一片,声震夜空。初一早晨,“开门炮”的一声“二踢脚”,凌空炸响,响彻天际。那时,我们这些孩童,哪里还睡得了懒觉,等天刚蒙蒙亮,就呼朋唤友出去疯了。小孩子们是最喜欢相互攀比的,聚到一起,先比比谁穿的新衣服好,再比比谁家门口的炮纸多,然后再比比谁拾的哑炮多。我们像一群小鸟,叽叽喳喳,从村东跑到村西,又从村南跑到村北……有时,还恶作剧地故意把点着的鞭炮埋藏在土堆里,或装入玻璃瓶,或扔到女孩子脚下,总之招来一顿骂,就都嬉笑着跑开了。当然,最倒霉的是放鞭炮炸了手,“砰”的一声,妈呀!当时一条胳膊就麻了,手掌被崩得漆黑,疼得龇牙咧嘴赶紧回家把手插进冰冷的水里,既不敢哭,也不敢告诉家里人。
初一早上吃完饺子,就开始给长辈拜年了。首先,爸妈领着我们姊妹几个先给爷爷奶奶磕头拜年,头不白磕,总有小白兔奶糖和五毛钱压岁钱。然后,再领着我们给本家的长辈们挨个拜年,当然这压岁钱不能少,有给2分的,有给5分的,最大的能给到1毛钱,有家境不好的,只能给把花生或瓜子等。回来的路上,我们见到年长的都要鞠躬问好,爸妈也微笑着和街上的人打招呼,好像人与人的感情一夜之间变得深了。即使往日相互之间存在隔阂恩仇,此时也都一笔勾销了。拜年真是一剂化解矛盾、增进感情的良药!当然,爸妈的5毛钱压岁钱更是不能少的。当我们几个口袋里攒有块儿八毛压岁“巨款”时,家人总是善意地提醒我们装好钱。我们总是提高警惕防备着,生怕爸妈给我们拿走,然后趁着家里没人,悄悄地把钱放在自认为最保密的地方,没事了就拿出来数一数。当然,小心翼翼保存一段时间,我们都是要如数上交的。毕竟,我们也知道家境的艰难。这时候,爸妈总会给我们都留1毛钱零花钱,让我们自由支配。
时光匆匆,岁月不居;童年的年,味道依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