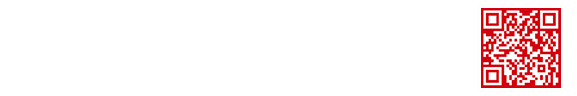我的家乡是豫西北的一个小山村。这里民风淳朴,生活节奏张弛有度。科技的日新月异,引领和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千百年沿袭下来的各种传统在时代的大浪中被淘洗冲刷,点点滴滴、曲曲折折地发生着改变。但是,还有一些习俗执拗地、经年不变地、看似毫无道理地传承下来。一个已埋在心中多年、却不知该如何看待的习俗,一直很想说道说道,那就是丧葬中的哭丧。
对于哭丧,原本我是极为厌恶的,而且决绝地认为是应该摒弃的。在我的老家,每每一户人家有人过世,子女亲戚都会很悲伤,忍不住哭泣。这原本是人之常情,但是大家评判子女的孝心和思念的标准却是哭的声音大不大,哭的时候有没有表达对逝去亲人的不舍,有没有说“舍不得呀,咋能抛下我们呀”之类的话,晓之以理,动之以礼,讲给大家听,做给大家看,感染周围的人,营造悲伤的氛围。如若不然,邻里就会多有微词,认为家里人都没有了,灵前连点响动都没有,这家的孩子太不像话,报以白眼和不屑。这样的评判标准导致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在守灵、送葬、亲戚友人吊唁等活动中,要不大家会从默默悲伤突然放声痛哭,撕心裂肺的声音中有些人是没有眼泪的;要不就是前来吊孝的一群不相干的亲戚正在说说笑笑,突然倒地就哭,捂着脸在大声地说道,别人却一句也听不清说道的是啥内容,而且最应景的就是只要有人劝,高亢的哭声会戛然而止,迅速恢复常态。那种假模假样,闹出了形形色色的笑话,有些甚至流传颇广。而且在哭丧中,承担主要角色的一般都是女人,女人的哭声仿佛决定着对逝去的亲人爱的程度。从小到大,我参加了很多这样的葬礼,让我深恶痛绝,觉得葬礼应该庄重肃穆,怎么能这样伪善和搞笑,这样的习俗就是陋习。
随着时间的推移,由我作为哭丧主角的葬礼,猝不及防地来了。先是我生命中对我最好、我最敬重和仰慕的父亲,突发心脏病不辞而别,像风一样消失在我的生活中。当时,母亲做了手术躺在医院里。父亲的离去,让我和弟弟不知所措,悲伤充盈心间,眼泪在奔涌,莫可名状的痛挥之不去。我们以农村最高的规格筹办着父亲的葬礼,可是我们家没有号啕大哭,没有大张旗鼓的悲怆。这给人的印象是好像我们不爱父亲。第一个不满意的是母亲。她生气地说:“你爸对你们多好,你们咋连哭一声都不会?你爸要是知道了,不知有多伤心。”我第一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原来,这大声的哭诉是可以慰藉母亲、告慰父亲的。我开始放声大哭,也开始絮絮叨叨地诉说只有自己听得懂的话。这些举动有些生涩,无法自然流露,但是我却没有极力反对,融入了哭丧习俗的大军,而且心甘情愿。
更没有想到的,是接下来我竟然努力地、主动地想成为哭丧的主角。父亲的离去,让母亲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她整日以泪洗面,加上自己也患了不治之症,在父亲三周年刚过就撒手人寰,追随父亲而去。这次我号啕大哭,再也不认为哭丧是作秀,是做给别人看,我要告诉母亲我很爱她,没有了她的故乡再也不是我的家,没有了爹娘,我的人生就再也没有来处,只剩归途。我想告诉她很多很多。几天的丧事期间,我认真地、努力地大哭,哭得头痛欲裂,喉咙沙哑,不为任何人,只为了让母亲在天有灵,能感受到她的孩子真的很爱她,同时让自己找到心灵的寄托,感到心安。
如今,家乡每天依然有生老病死,哭丧的习俗依然还在传承和延续。虽然年轻一代已经不屑于这种做法,但是我却再也没有认为这是陋习,也不再认为必须摒弃它。存在就有它的合理性,也许还有很多人需要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