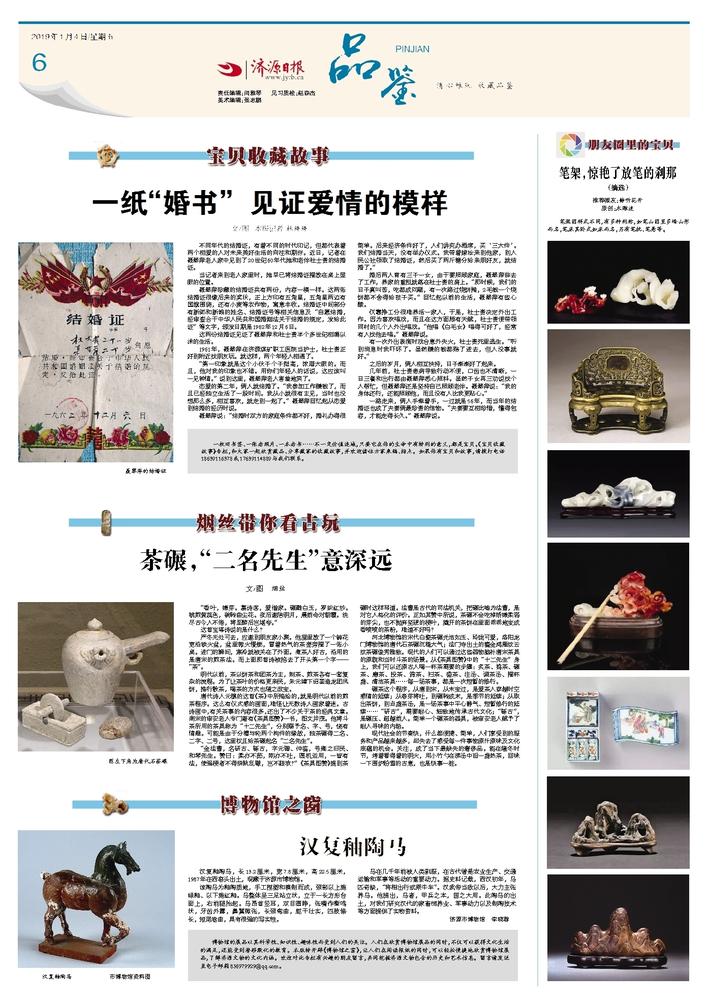“香叶,嫩芽。慕诗客,爱僧家。碾雕白玉,罗织红纱。铫煎黄蕊色,碗转曲尘花。夜后邀陪明月,晨前命对朝霞。洗尽古今人不倦,将至醉后岂堪夸。”
这首宝塔诗说的是什么?
严冬无处可去,应邀到朋友家小聚。他屋里放了一个铸花宽沿铁火盆,盆里微火慢燃,冒着热气的茶壶旁摆了一张小桌。进门的瞬间,寒冷就被关在了外面。煮茶人好古,沿用的是唐宋的煎茶法。而上面那首诗被掐去了开头第一个字——“茶”。
明代以前,茶以饼茶和团茶为主,制茶、煎茶各有一套复杂的流程。为了让茶叶的价格更亲民,朱元璋下诏罢造龙团凤饼,推行散茶,喝茶的方式也随之改变。
唐代诗人元稹的这首《茶》中所描绘的,就是明代以前的煎茶程序。这么有仪式感的画面,难怪让无数诗人画家着迷。古诗画中,有关茶事的内容很多,还出了不少关于茶的经典文章。南宋的审安老人专门著有《茶具图赞》一书,图文并茂。他将斗茶所用的茶具称为“十二先生”,分别赐予名、字、号,饶有情趣。可能是由于分槽与轮两个构件的缘故,独茶碾得二名、二字、二号,这里权且给茶碾起名“二名先生”。
“金法曹,名研古、轹古,字元锴、仲鉴,号雍之旧民、和琴先生。赞曰:柔亦不茹,刚亦不吐,圆机运用,一皆有法,使强梗者不得殊轨乱辙,岂不韪欤?”《茶具图赞》提到茶碾时这样写道。法曹是古代的司法机关,把碾比喻为法曹,是对它人格化的评价。正如其赞中所说,茶碾不会吃掉娇嫩柔弱的芽尖,也不抛弃坚硬的梗叶,撬开的茶饼在里面乖乖地变成香喷喷的茶粉,难道不好吗?
河北博物馆的宋代白瓷茶碾光洁如玉、玲珑可爱,洛阳龙门博物馆的唐代石茶碾沉稳大气;法门寺出土的鎏金鸿雁纹云纹茶碾俊秀雅致。现代的人们可以通过这些器物脑补唐宋茶具的原貌和当时斗茶的场景。从《茶具图赞》中的“十二先生”身上,我们可以还原古人喝一杯茶需要的步骤:炙茶、捣茶、碾茶、磨茶、投茶、筛茶、扫茶、盛茶、注汤、调茶汤、摆杯盏、清洁茶具……每一场茶事,都是一次短暂的修行。
碾茶这个程序,从唐到宋,从未变过,是爱茶人穿越时空感情的延续;从春芽将吐,到碾转成末,是季节的延续;从取出茶饼,到点盏茶汤,是一场茶事中平心静气、短暂修行的延续……“研古”,需要耐心、细致地传承古代文化;“轹古”,是碾压、超越前人。简单一个碾茶的器具,被审安老人赋予了耐人寻味的内涵。
现代社会的节奏快,什么都便捷、简单,人们享受到的服务和产品越来越多,却失去了感受每一件事物原汁原味及文化底蕴的机会。关注,成了当下最缺失的奢侈品。能在隆冬时节,烤着看得着的明火,用小竹勺在沸汤中舀一盏热茶,回味一下围炉盼雪的古意,也是快事一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