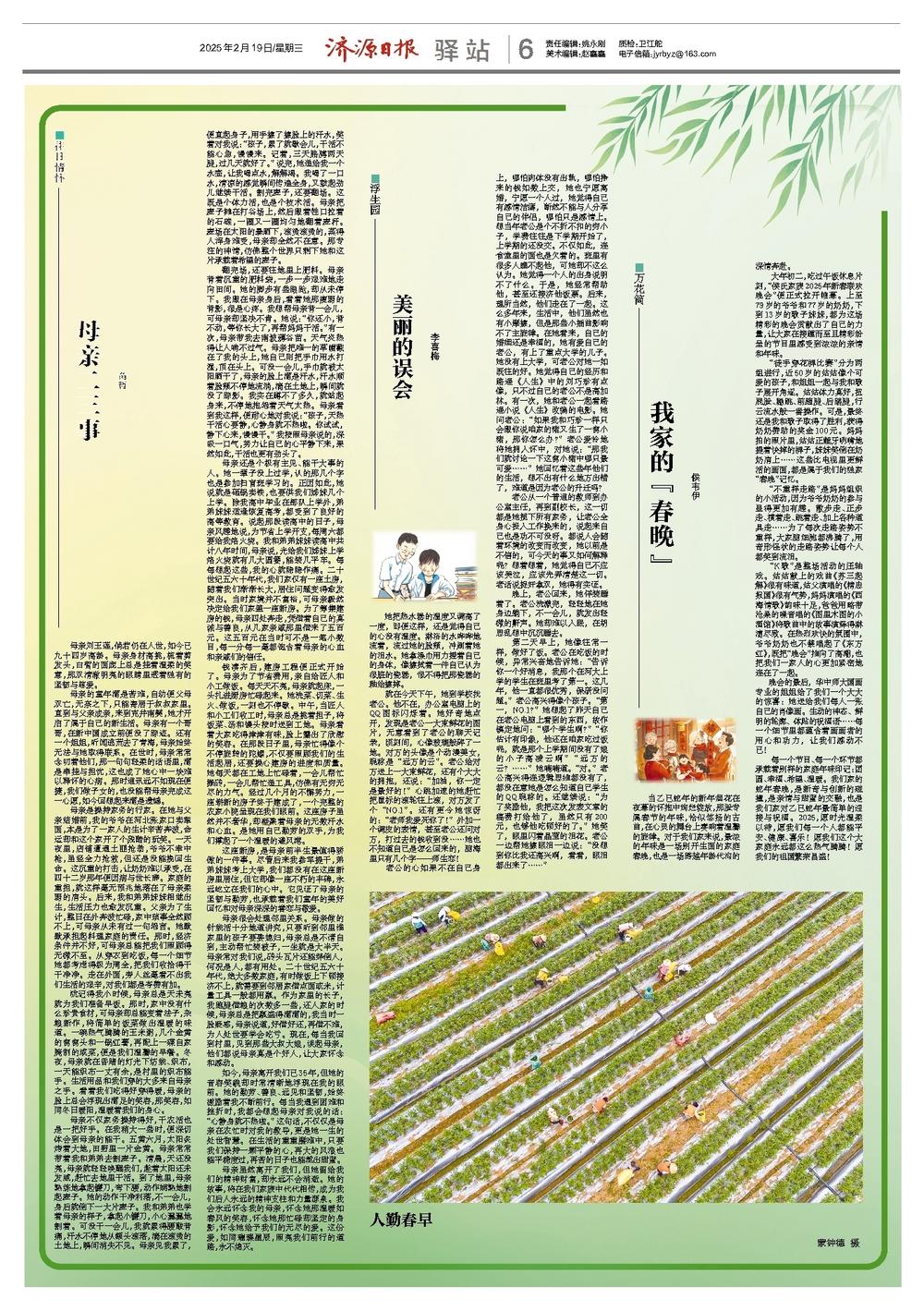母亲刘玉莲,倘若仍在人世,如今已九十四岁高龄。母亲身材高挑,梳着剪发头,白皙的面庞上总是挂着温柔的笑意,那双清澈明亮的眼睛里透着独有的坚韧与慈爱。
母亲的童年满是苦难,自幼便父母双亡,无奈之下,只能寄居于叔叔家里。直到与父亲成亲,来到克井南樊,她才开启了属于自己的新生活。母亲有一个哥哥,在新中国成立前便没了踪迹。还有一个姐姐,听闻逃荒去了青海,母亲始终无法与她取得联系。在世时,母亲常常念叨着他们,那一句句轻柔的话语里,满是牵挂与担忧,这也成了她心中一块难以释怀的心病。那时通讯远不如现在便捷,我们做子女的,也没能帮母亲完成这一心愿,如今回想起来满是遗憾。
母亲是操持家务的行家。在她与父亲结婚前,我的爷爷在河北张家口卖犁面,本是为了一家人的生计辛苦奔波,命运却和这个家开了个残酷的玩笑。一天夜里,店铺遭遇土匪抢劫,爷爷不幸中枪,虽经全力抢救,但还是没能挽回生命。这沉重的打击,让奶奶难以承受,在四十二岁那年便因病与世长辞。家庭的重担,就这样毫无预兆地落在了母亲柔弱的肩头。后来,我和弟弟妹妹相继出生,生活压力也愈发沉重。父亲为了生计,整日在外奔波忙碌,家中琐事全然顾不上,可母亲从未有过一句怨言。她默默承担起料理家庭的责任。那时,经济条件并不好,可母亲总能把我们照顾得无微不至。从穿衣到吃饭,每一个细节她都考虑得极为周全,把我们收拾得干干净净。走在外面,旁人丝毫看不出我们生活的艰辛,对我们都是夸赞有加。
犹记得我小时候,母亲总是天未亮就为我们准备早饭。那时,家中没有什么珍贵食材,可母亲却总能变着法子,杂粮新作,将简单的饭菜做出温暖的味道。一碗热气腾腾的玉米粥,几个金黄的窝窝头和一锅红薯,再配上一碟自家腌制的咸菜,便是我们温馨的早餐。冬夜,母亲就在昏暗的灯光下纺线、织布, 一天能织布一丈有余,是村里的织布能手。生活用品和我们穿的大多来自母亲之手。看着我们吃得好穿得暖,母亲的脸上总会浮现出满足的笑容,那笑容,如同冬日暖阳,温暖着我们的身心。
母亲不仅家务操持得好,干农活也是一把好手。在我稍大一些时,便深切体会到母亲的能干。五黄六月,太阳炙烤着大地,田野里一片金黄。母亲常常带着我和弟弟去割麦子。清晨,天还没亮,母亲就轻轻唤醒我们,趁着太阳还未发威,赶忙去地里干活。到了地里,母亲熟练地拿起镰刀,弯下腰,动作娴熟地割起麦子。她的动作干净利落,不一会儿,身后就倒下一大片麦子。我和弟弟也学着母亲的样子,拿起小镰刀,小心翼翼地割着。可没干一会儿,我就累得腰酸背痛,汗水不停地从额头滚落,滴在滚烫的土地上,瞬间消失不见。母亲见我累了,便直起身子,用手擦了擦脸上的汗水,笑着对我说:“孩子,累了就歇会儿,干活不能心急,慢慢来。记着,三天胳膊两天腿,过几天就好了。” 说完,她递给我一个水壶,让我喝点水,解解渴。我喝了一口水,清凉的感觉瞬间传遍全身,又鼓起劲儿继续干活。割完麦子,还要翻场。这既是个体力活,也是个技术活。母亲把麦子摊在打谷场上,然后跟着牲口拉着的石磙,一圈又一圈均匀地翻着麦秆。麦场在太阳的暴晒下,滚烫滚烫的,蒸得人浑身难受,母亲却全然不在意。那专注的神情,仿佛整个世界只剩下她和这片承载着希望的麦子。
翻完场,还要往地里上肥料。母亲背着沉重的肥料袋,一步一步艰难地走向田间。她的脚步有些踉跄,却从未停下。我跟在母亲身后,看着她那瘦弱的背影,很是心疼。我想帮母亲背一会儿,可母亲却坚决不肯。她说:“你还小,背不动,等你长大了,再帮妈妈干活。”有一次,母亲带我去南坡薅谷苗。天气炎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母亲把唯一的草帽戴在了我的头上,她自己则把手巾用水打湿,顶在头上。可没一会儿,手巾就被太阳晒干了,母亲的脸上满是汗水,汗水顺着脸颊不停地流淌,滴在土地上,瞬间就没了踪影。我实在蹲不了多久,就站起身来,不停地抱怨着天气太热。母亲看到我这样,便耐心地对我说:“孩子,天热干活心要静,心静身就不热啦。你试试,静下心来,慢慢干。” 我按照母亲说的,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果然如此,干活也更有劲头了。
母亲还是个极有主见、能干大事的人。她一辈子没上过学,认的那几个字也是参加扫盲班学习的。正因如此,她说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我们姊妹几个上学。除我高中毕业在部队上学外,弟弟妹妹适逢恢复高考,都受到了良好的高等教育。说起那段读高中的日子,母亲风趣地说,为节省上学开支,每周六都要给我烙火烧。我和弟弟妹妹读高中共计八年时间,母亲说,光给我们姊妹上学烙火烧就有几大圆篓,能装几平车。每每想起这些,我的心就隐隐作痛。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家仅有一座土房,随着我们渐渐长大,居住问题变得愈发突出。当时家境并不富裕,可母亲毅然决定给我们家盖一座新房。为了筹集建房的钱,母亲四处奔走,凭借着自己的真诚与善良,从几家亲戚那里借来了五百元。这五百元在当时可不是一笔小数目,每一分每一毫都饱含着母亲的心血和亲戚们的信任。
钱凑齐后,建房工程便正式开始了。母亲为了节省费用,亲自给匠人和小工做饭。每天天不亮,母亲就起床,一头扎进厨房忙碌起来。她洗菜、切菜、生火、做饭,一刻也不停歇。中午,当匠人和小工们收工时,母亲总是挑着担子,将饭菜、汤和馒头按时送到工地。母亲看着大家吃得津津有味,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在那段日子里,母亲忙得像个不停旋转的陀螺,不仅要照顾我们的生活起居,还要操心建房的进度和质量。她每天都在工地上忙碌着,一会儿帮忙搬砖,一会儿帮忙递工具,仿佛有无穷无尽的力气。经过几个月的不懈努力,一座崭新的房子终于建成了,一个完整的农家小院呈现在我们眼前。这座房子虽然并不奢华,却凝聚着母亲的无数汗水和心血。是她用自己勤劳的双手,为我们撑起了一个温暖的避风港。
这座新房,是母亲前半生最值得骄傲的一件事。尽管后来我参军提干,弟弟妹妹考上大学,我们都没有在这座新房里居住,但它却像一座不朽的丰碑,永远屹立在我们的心中。它见证了母亲的坚韧与勤劳,也承载着我们童年的美好回忆和对母亲深深的眷恋与敬爱。
母亲很会处理邻里关系。母亲做的针线活十分地道讲究,只要听到邻里谁家里的孩子要娶媳妇,母亲总是不请自到,主动帮忙装被子,一坐就是大半天。母亲常对我们说,砖头瓦片还能绊倒人,何况是人,都有用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绝大多数家庭,有时做饭上下顿接济不上,就需要到邻居家借点面或米,计量工具一般都用瓢。作为家里的长子,我跑腿借粮的次数多一些,还人家的时候,母亲总是把瓢盛得满满的,我当时一脸疑惑,母亲说道,好借好还,再借不难,为人处世要学会吃亏。现在,每当我回到村里,见到那些大叔大娘,谈起母亲,他们都说母亲真是个好人,让大家怀念和感动。
如今,母亲离开我们已35年,但她的音容笑貌却时常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她的勤劳、善良、远见和坚韧,始终激励着我不断前行。每当我遇到困难和挫折时,我都会想起母亲对我说的话:“心静身就不热啦。” 这句话,不仅仅是母亲在农忙时对我的教导,更是她一生的处世智慧。在生活的重重磨难中,只要我们保持一颗平静的心,再大的风浪也能平稳度过,再苦的日子也能熬出甜蜜。
母亲虽然离开了我们,但她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却永远不会消逝。她的故事,将在我们家族中代代相传,成为我们后人永远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我会永远怀念我的母亲,怀念她那温暖如春风的笑容,怀念她那忙碌却坚定的身影,怀念她给予我们的无尽的爱。这份爱,如同璀璨星辰,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永不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