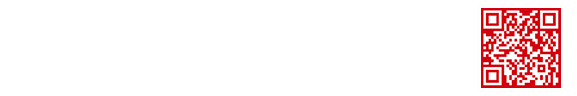早上起来,母亲已经把饭做好了。
天气阴沉沉的。母亲说河南电视台预报今天可能会有小雨或雨夹雪,我查了查手机,天气是一会儿一变,时而阴天,时而有雨。孩子问什么时候能下雪,我抬头看看天,天空安静得很。我也在期待一场雪。
吃完饭,我和孩子一起去街上赶集。天气冷了,家里的门帘还没有挂上,本想着这暖和的天气将持续下去,眼瞅着春天就要来了。可到底是四九天气,这股冷空气终于要将雪吹下来了。
骑着三轮车刚出门转过路口,就遇到了邻居二婶。她在前边走,听到我和孩子的说话声,转回头问:“回来过年了?”
“嗯,你上哪儿去呀?”我刹车停下来。
“去看看肉啥价。”接着,她面对孩子问:“不走了吧?”
“不走了,就在家里过年嘞!”孩子干脆地回答。
一路赶到街上。街上的人也不算多,来回过往的路人行色匆匆,路边一群男人围着一堆火在天南地北地闲聊。他们当中,有的人我认识,有的脸熟,当然也有陌生人。我走进百货商店,店里没有人,于是对着那群闲聊的男人,把当家的从人堆里叫回来,问了门帘的价钱,又买了一些其他物件,孩子扫码付钱,我们便一起打道回府。
转向回还,在妻子单位门口又遇到了她单位里的熟人,虽然不知道叫什么,但平时都叫嫂子。
“回来过年了?不走了吧?”
“不走了。你在干啥嘞?”
“蒸馍嘞!拾点柴火。”她腰上系着枣红色的围裙,手里拿了很多的柴火。每到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都要蒸馒头,她说外边卖的怎能有自己蒸的好吃呢!走嫂子家门口,孩子悄悄地凑到我耳边,小声地问:“你咋认识那么多人?”我说:“都是乡里乡亲,都是熟人。”
刚回到院子里,脚没落地,九队的玲花就从院外边进来,要找母亲。
“你妈嘞?”她袖子上戴着袖套,手上还粘着面。
“妈!有人找你!”我朝屋里喊,和孩子一起准备卸下我们买的东西。
母亲正在屋里看电视,听见我的声音从屋里迎了出来,只听见玲花说:“你还保存有面头儿(面起子)吗?”
“还有,等一下,我给你拿。”母亲径直走进了厨房。
玲花走后,我便开始着手挂门帘,找锤子、找钉子、搬梯子。正起劲儿忙活,隔壁玉珍也来找母亲。
母亲回头问:“咋了?玉珍。”
“这不是在家里蒸馍,放了碱,把面醒好了,不知道放的碱量合适不合适,叫你去拿拿。”玉珍操着手,她的头发应该是新做的,板型很正,很时髦。
“你这成天蒸类,忘了?”母亲把工具递给我,起身拍了拍袖子上的尘土,准备去看看。
“哪呢!我也有半年没有蒸了。过年呢,又怕拿不准,蒸不好丢人现眼,这不,叫你去看看!”
说话间,母亲已和玉珍一起向她家走去。
我一个人挂门帘。本指望着孩子给我帮忙,可是他就像一只卧不稳的兔子,一会儿都不知道窜哪里了,好在这活也不是很累人,只是上上下下不方便而已。
下午两点多,我在路上瞎逛,遇到我的妗子去理发,说晚上和我母亲一起去洗澡,让我早点做饭。回到家,我便跟母亲说了妗子的约定。母亲说:“早就约好了。走,去帮忙炸丸子!”往年年前,家里的其他人都各忙各的,只有我和母亲两个人在家里忙前忙后。今年,哥哥、嫂子得空,一早就盘好了肉馅,我和母亲一起去帮忙。
抬火炉、拿大盆、搬桌子,一切准备就绪,刚把火点着,孩子从外边冲了进来:“下雪了!下雪了!”我推门看去,鹅毛大的雪轻盈地飘落下来,落地即逝,与微尘一起升腾出冬的味道。房子、树木、烟囱、铁路……都被大大小小的雪片笼罩着,这是今冬我见到的第一场雪。孩子因为下雪高兴得满怀期待:明天早上我们一起打雪仗吧!
明天早上会有厚厚的雪吗?我不忍心打破他的欢愉。于是,我也期待明天能继续下雪,洋洋洒洒、酣畅淋漓地下一场大雪!
灶膛里的火舔着锅底,丸子在油锅里“滋滋”作响,到底是人多好办事,以前我和母亲要忙活一下午,今天一个多小时就结束了。孩子们喊着还想吃鸡柳,母亲说:“早就给你们准备了!”
天渐渐暗了下来,而我心里关于年的念想也在逐渐升温,不仅仅是因为那一丝一缕的乡音乡情,还有一场及时的瑞雪。有了一场雪才叫冬天,有了一场忙才是过年!
雪,真正拉开了春的序曲,浓浓的期许,昭昭如愿,岁岁安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