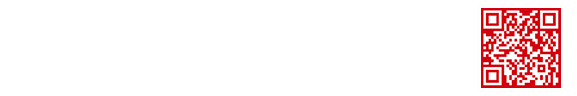我是一瓣素白的雪,迎着芳冽的风,在晨星下醉舞,在霓虹里绽放一生的孤傲。
我是黛玉葬别的洁白,是文成公主眼中流出的清泪,是广寒宫的古筝迸发出的玄妙音符。黄河里奔流着我不眠的魂魄。
王屋的多情,注定不会因我而冰冷;蟒河的缠绵,注定不会因我而沉寂。失去青春的血色,逆着空旷的光,渐渐睡去。在残存的落叶中淡化了表情。
我以止水的姿态,度化满目青山。以相思的叶脉,漂写我卑微的颠簸。我摒弃了预约的客船,在鼓浪屿的古巷里,熬尽我一冬的积蓄。
我灼伤的翎羽,是我的热切。我的瞳仁里,盛满了猎猎的铃声。
灿然的枝头,燃烧着你的眼睫;一河的潇洒,熟稔了你的行囊;膨胀的琼楼,柔软了你的风骨;裸露的襟怀,堆砌了一个又一个卖火柴的小女孩。
长发和裙裾的倩影,追逐着夸父的脚步,吟唱着雪狼一样的欢愉。
微风中的柳丝,在乌云的缝隙里,窥见了曙光。一任蜡烛的泪,在臂膀上茁壮。
你执着的呼吸里,把长城万里的万里信念,披上霞装。于寒冷的洗礼中,温热了一方净土的生长。
白鹭
静如镜面的蟒河,倒映出她的英姿,曼妙、优雅、娴静。
进入三九的天气,寒冷入骨。她却无所畏惧,专注传情,旁若无物。
一只白鹭,梦一样的白鹭。在愚公桥东,有一拦水皮坝,河水从久已坍塌的坝上缓缓流过。
一只挽着风的白鹭,久久地、定定地站立着。如同一座雕塑。任凭流水打着旋儿,从双腿间滑过,激起一首首歌谣。
一只踩着阳光的白鹭,盯着水面,偶尔转动高视的头颈。那黄红的喙,跟着移动。她在扫描着水中的猎物,期盼着美味的鱼儿游过。
白白的蓑羽,被晨光写意成一团锦缎;长长的颈项,弯曲成一件汉白玉。
淡淡的白鹭,检阅着流水,检阅着游鱼,检阅着流逝的光影。孜孜不倦。
半个月的光景,我发现她都在同一个位置盯着,把自己盯成一束回忆。如烟如雾,身披白纱,小女子一般。
又一个早上,没了白鹭的踪迹。不一会儿,她从西边飞来,滑翔一个漂亮的弧线,又落到原来的地点。她去衔春了吧,刚刚回归。
素洁的白鹭,将细碎的微笑,叠成几缕波纹,偷听水底鱼儿们轻喃呢语,谈情说爱。
她在守望着纯情故事?还是在惋惜逝去的拥有?也像在祭奠斑驳而青涩的旧时光?
她孤独的,痴迷的,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去,面水而居。
她在演绎守水待鱼吧。
这一河清明的春水啊。白鹭嗅到了早春的气息,仿佛看见了春暖花开……
梧桐
亭亭梧桐静立着。世纪广场寥寥的。
梧桐裸露着身心,释放逼人的寒气。虽很无语,但很威严。
一只青鸟,站在枝头。与仅有的一片红叶对话。也像为无语的梧桐唱着情歌。
灵动的青鸟,凝视着单薄,凝视着瘦骨嶙峋;咀嚼着失传的古歌,咀嚼着绿色的足音。
这片红叶像旗帜,虽然是残留的,却不惧腊月的风,不惧深沉的伤。它要见证残酷,做最后的飞翔。
青鸟缠绵地低语,抚慰着红色的伤,细数拧不干的思念,丈量相知的星光,留恋羞怯的笑颜。尽管唇齿交错,却很灿烂。
流浪的云,干净的蓝,点醉了霜晨月。
梧桐守候落雪的归期,守候梅花般的清香。
青鸟化成了凤凰,落雪为她们喷洒下盛大的礼花。
垂柳
蟒河边,一排垂柳,轻飏着满头发丝。
作清风的姿势,作流云的姿势,作七彩练的姿势。
如酒的黄昏里,洗沐着疲惫,洗沐着笑语,洗沐着安宁。
凛冽的寒风,疏落了秀气,离间了叶片的紧密,却未曾改变如剑的骨骼,如线的腰肢。
垂柳一如窈窕少女,默默宣读着生命的誓言,梳理着自己的形象。与蓝天拥吻的渴望,蠢蠢欲动。
寒风在垂柳的怀里哭泣。他们痛恨自己扼杀了垂柳的色彩,剥夺了叶片存在的权利。那是蛾眉般的娇容啊,那是洋溢的青春,那是永恒的主题。
每一片枝叶,在由绿到黄的蜕变里,看清了世界,也看清了自己。懂得了萌芽的价值,也储备着翠绿的激情。
每一条根茎,都是交错的痛,比死亡更深刻、更黑暗的痛。也都是延展的起点,是坚强的突破。
垂柳从容淡定的性格,与流水一起,抒写着明媚,抒写自由的元素,抒写着奔涌的岁月。
天空中有惊鸿的影子,款款掠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