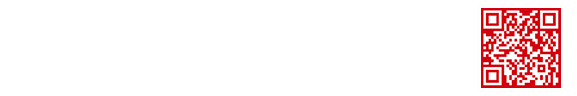初冬的早晨,被薄雾笼罩着的小山村一片沉寂。顺着山梁住的四户人家,窑洞的门都紧闭着。院墙外,鸡圈里的公鸡已经打了两遍鸣,牛圈里的大黄牛也开始有一搭没一搭地反刍,只有猪还在呼呼地睡着觉。
这时,只听“吱扭”一声,二叔家的屋门打开了。不一会儿,二叔敲着盛着猪食的搪瓷盆,“唠唠、唠唠”地吆喝他家的大黑猪过来吃食。
“你二叔这么早就喂猪呢?是要去下冶卖猪哩吧?”母亲听到二叔的喊声,一边胡乱梳着头发,一边往隔壁二叔家走去。
卖猪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农民可是件大事。头一年就要到黄河南岸的西沃集上“逮”个小猪娃,当他们把“唧唧”叫的小猪娃背在肩上时,心里被明年这时候要卖一头大肥猪的美好愿望充斥着,一点也不觉得累。他们脚下的步子轻盈起来,肩上背着的仿佛是一捆毛毛块块卖猪的钞票。
喂猪的重任一般都落在妇女身上。小猪娃一个难养,两个在一起就抢着吃食。二叔去年就逮了两个小猪娃,准备养大了给儿子娶媳妇,一头卖钱给儿媳妇送彩礼,一头留着婚宴上杀了待亲。一转眼一年过去了,二叔家秋成哥准备腊月十七结婚,给亲家的“好”都送过了,只等卖了大黑猪,去送彩礼。
山坳里的几家邻居都围上去给二叔拉话。小爷说:“别光给猪吃这稀汤寡水,一泡尿拉的,掉秤几斤。”母亲说:“红薯南瓜难消化,两个钟头把猪赶到下冶,秤上保准不亏。”小叔说:“不如给猪炒几斤玉米粒吃,到路上渴了再让它喝些水,肚皮撑得圆鼓鼓的,还怕不上秤?”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给二叔出主意。二叔忙让二婶照着法子给猪做各种吃食。
大黑猪在惺忪中被各种美食伺候一番,终于可以上路了。二叔准备好了架子车,大家齐心协力把猪赶到车上。这时,太阳已升起一竿子高,孤零零地挂在东边的天空,发出明晃晃的冷光。二叔拉着架子车沿着坑坑洼洼的山路,艰难前行。车上的大黑猪随着每一次颠簸发出“哼哼唧唧”的抗议声。二叔的脊背上一会儿就冒出了汗,呼出的白气刚罩着嘴唇就不见了。
“滴,滴……”正当二叔拉着车埋头赶路时,身后传来了卡车的鸣笛声。二叔刚想让路,同村的太虎叔就从驾驶室里跳了下来,招呼二叔把黑猪弄到卡车壳篓里。原来太虎叔刚好要到下冶煤矿拉煤,顺便帮二叔把猪送到食品站。二叔和二婶也坐到驾驶室的时候,心里别提多感激了。二婶暗暗地盘算一番,30多里的山路,一下子提前一个多小时到食品站,早上喂猪吃的一肚子食,说啥也化不成屎尿屙出来,都是秤上的猪肉钱。
山路随着山势盘旋,路面因了雨水的冲刷与大卡车的碾压,显得沟壑纵横凹凸不平。太虎叔两手死死地抓着方向盘,好像车辆的颠簸随时会让他失去对方向盘的控制。二婶和二叔的身体被抛起来又落下去,好几次二叔的头都磕在了驾驶室的内顶上。驾驶室里弥漫着刺鼻的柴油味,发动机“轰隆隆”的声音,车轮与地面“咣当”撞击的声音,这一切让二婶胃里翻江倒海地难受,头也疼得厉害。
好不容易熬到了下冶食品站,二叔冲下驾驶室,身一跃爬上卡车壳篓。只见卡车壳篓里空空荡荡,一根猪毛也没有,眼前的状况顿时让他惊叫起来:“猪哩,猪哩,我的猪咋没有了?”太虎叔也跃上卡车,“猪被甩下车了!”太虎叔大喊起来。二婶听闻此言,腿抖得蹬不住车身,一下子瘫坐在了地上。“老天爷,我的猪哪儿了?”二婶放声大哭。“哭有啥用,赶紧沿路寻猪去。”二叔使劲拽起二婶说。
二叔和二婶跌跌撞撞沿着来时的路,仔细地辨认地上是否有猪摔下来的痕迹。是摔死了,还是摔下来跑到路边的地里了?这真是活要见猪,死要见尸。他俩的眼都快瞪瞎了,嘴里“唠唠、唠唠”地叫个不停,口干舌燥。30多公里的山路,才找了不到十分之一,就如大海捞针一样。路上的行人听说了他们的遭遇,说这样找下去可不行,得多叫些人来。二叔让二婶继续找,他沿着村庄找亲戚来帮忙。
曹腰二叔的表姑家,探马庄二婶的老舅家,小横岭二叔的妹妹家。这样通报下来,找猪的队伍壮大起来,这个山头那个山洼里,“唠唠”的叫猪声此起彼伏。
太阳不知什么时候已到了西山头上。山尖尖努力地撑着它,仿佛一不留神就掉下去一样。折腾了半天,找猪的人们精疲力尽,灰头土脑。有的一屁股坐在堰头上,看着西边的太阳发呆。有的爬上一棵柿子树,把上面秋天剩余的一个空柿子摘了下来吃。
正当人们准备放弃的时候,二叔在探马庄的亲戚传来了好消息,说有人在公路边地里的玉米秆下发现一头大黑猪。二叔二婶赶忙跑去辨认,只见大黑猪在玉米秆堆里拱出个猪窝,正拖着受伤的后腿,惊恐地看着周围的人。二叔看见了大黑猪,“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向大黑猪连连作揖,哭得像大花脸一样的二婶也破涕为笑。
天黑了下来,二叔和二婶赶着猪住到了探马庄的亲戚家。夜里亲戚家的邻居听说这件事,过来给二叔说:“我在下冶食品站有熟人,明天我帮你把这猪卖个好价钱。”
当时,猪的等级要求“森严”,只有膘肥体壮、毛色光亮的猪才能划到一等级别,别看一等和二等一斤差几毛钱,一百多斤的猪算下来几十块钱就差出来了。二叔再一次喜出望外,感谢的话说了一大堆。第二天,在亲戚邻居的陪同下,二叔家这头瘸腿的大黑猪,被食品站的工作人员划上了一等价。一共卖了120块钱,亲戚的邻居让二叔借他40块钱用,说过几天就还他,这40块钱刚好是一等猪和二等猪的差价。二叔没有半点犹豫就答应了。
亲戚的邻居口中的很多个“几天”过去了,他一点还钱的意思都没有。二叔跑去他家要了几回,每次都被亲戚邻居以各种借口搪塞过去。
二叔给秋成哥办完婚礼,又逮了小猪娃,猪娃长到半大时,秋天的玉米都成熟了。二叔拉着架子车到亲戚的邻居家要玉米“顶账”,“这次看你还有啥理由不给呢?”二叔一边拉车一边嘟囔道。
在二叔看来十拿九稳的事儿,结果出乎意料,亲戚的邻居既没有还钱,也不舍得用玉米顶账,只是大包大揽让二叔再卖猪时还找他。凭他的关系,无论猪养得咋样,都能卖个好价钱!
回到家,二叔向二婶声明:“人的命,自己定,再卖猪了,亏死也不托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