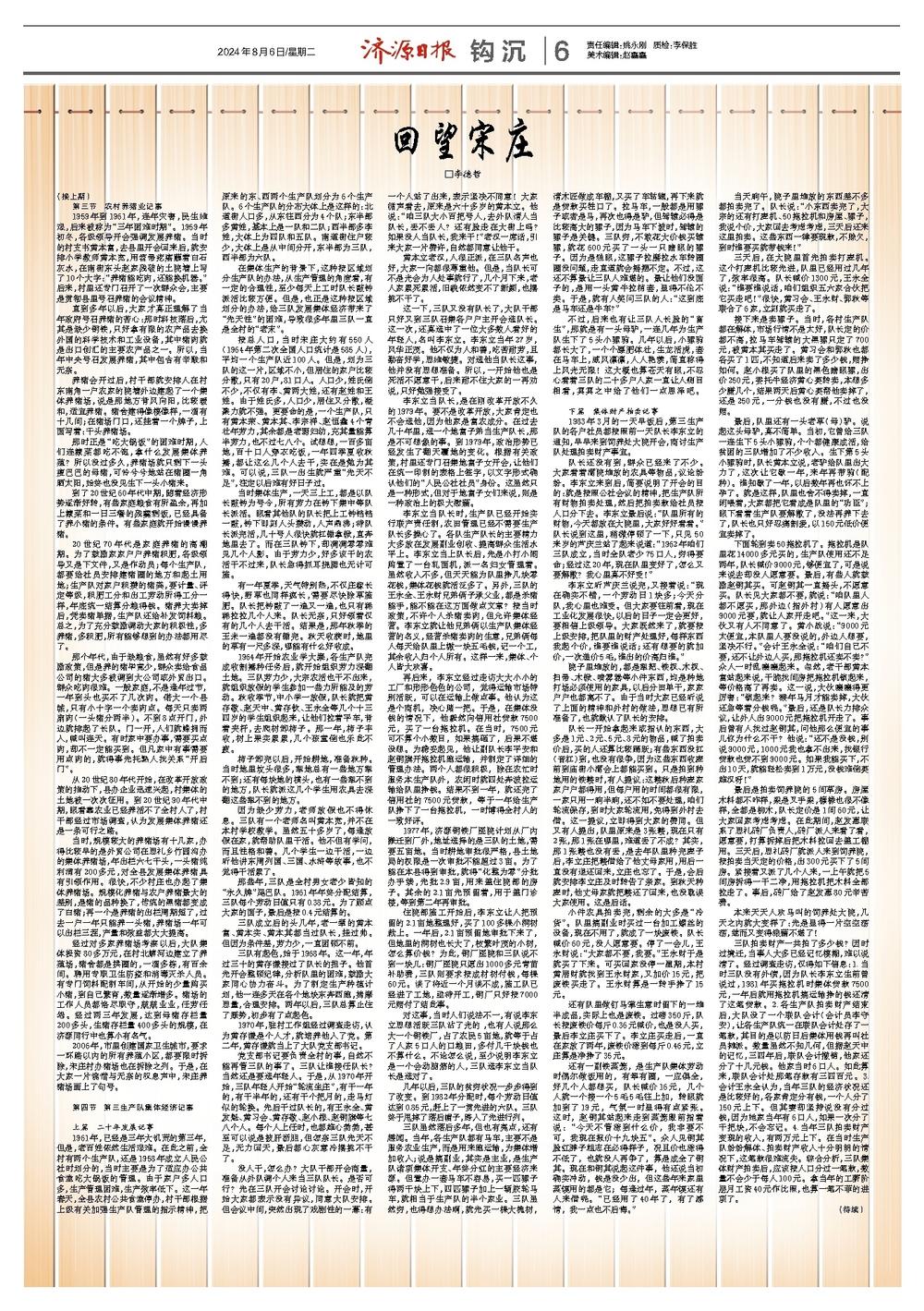(接上期)
第三节 农村养猪业记事
1959年到1961年,连年灾害,民生维艰,后来被称为“三年困难时期”。1959年初冬,各级领导开会强调发展养猪。当时的村支书黄本富,去县里开会回来后,就安排小学教师黄本宽,用笤帚疙瘩蘸着白石灰水,在南街东头赵家残破的土院墙上写了10个大字:“养猪能吃肉,还能换机器。”后来,村里还专门召开了一次群众会,主要是贯彻县里号召养猪的会议精神。
直到多年以后,大家才真正理解了当年政府号召养猪的苦心:那时科技落后,尤其是缺少钢铁,只好拿有限的农产品去换外国的科学技术和工业设备,其中猪肉就是出口创汇的主要农产品之一。所以,当年中央号召发展养猪,其中包含有辛酸和无奈。
养猪会开过后,村干部就安排人在村东南角一户农家的院墙外边建起了一个集体养猪场,说是那地方背风向阳,比较暖和,适宜养猪。猪舍建得像模像样,一溜有十几间;在猪场门口,还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千头养猪场。
那时正是“吃大锅饭”的困难时期,人们连糠菜都吃不饱,拿什么发展集体养殖?所以没过多久,养猪场就只剩下一头瘦巴巴的母猪,可怜兮兮地站在猪圈一角晒太阳,始终也没见生下一头小猪来。
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随着经济形势逐渐好转,有些家庭粮食有所盈余,再加上糠菜和一日三餐的残羹剩饭,已经具备了养小猪的条件。有些家庭就开始慢慢养猪。
20世纪70年代是家庭养猪的高潮期。为了鼓励家家户户养猪积肥,各级领导又是下文件,又是作动员;每个生产队,都要给社员安排建猪圈的地方和起土用地;生产队对家户积攒的猪粪,要计量、评定等级,积肥工分和出工劳动所得工分一样,年底统一结算分粮得钱。猪养大卖掉后,凭卖猪单据,生产队还给补发饲料粮。总之,为了充分鼓励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多养猪,多积肥,所有能够想到的办法都用尽了。
那个年代,由于缺粮食,虽然有好多鼓励政策,但是养的猪毕竟少,群众卖给食品公司的猪大多被调到大公司或外贸出口。群众吃肉很难。一般家庭,不是逢年过节,一年到头也买不了几次肉。偌大一个县城,只有小十字一个卖肉点。每天只卖两扇肉(一头猪分两半)。不到8点开门,外边就排起了长队。门一开,人们就蜂拥而入,喊叫连天。有时家中要办事,需要买点肉,却不一定能买到。但凡家中有事需要用点肉的,就得事先托熟人找关系“开后门”。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下,县办企业迅速兴起,村集体的土地被一次次征用。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眼看靠农业已经养活不了全村人了,村干部经过市场调查,认为发展集体养猪还是一条可行之路。
当时,规模较大的养猪场有十几家,办得比较早的是外贸公司在思礼乡竹园沟办的集体养猪场,年出栏六七千头,一头猪纯利润有200多元,对全县发展集体养猪具有引领作用。很快,不少村庄也办起了集体养猪场。规模化养猪与农户养猪最大的差别,是猪的品种换了,传统的黑猪都变成了白猪;再一个是养猪的出栏周期短了,过去一户一年只能养一头猪,养猪场一年可以出栏三茬,产量和效益都大大提高。
经过对多家养猪场考察以后,大队集体投资80多万元,在村北蟒河边建立了养殖场,猪舍都是拱圈的,一溜多栋,有百余间。聘用专职卫生防疫和消毒灭杀人员。有专门饲料配制车间,从开始的少量购买小猪,到自己繁育,数量逐渐增多。猪场的工作人员都恪尽职守,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经过两三年发展,达到母猪存栏量200多头,生猪存栏量400多头的规模,在济源同行中也算小有名气。
2006年,市里创建国家卫生城市,要求一环路以内的所有养殖小区,都要限时拆除,宋庄村办猪场也在拆除之列。于是,在大家一片惋惜与无奈的叹息声中,宋庄养猪场画上了句号。
第四节 第三生产队集体经济记事
上篇 二十年发展记事
1961年,已经是三年大饥荒的第三年,但是,老百姓依然生活艰难。在此之前,全村有两个生产队,还是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时划分的,当时主要是为了适应办公共食堂吃大锅饭的管理。由于家户多人口多,生产管理困难,生产效率低下。这一年春天,全县农村公共食堂停办,村干部根据上级有关加强生产队管理的指示精神,把原来的东、西两个生产队划分为6个生产队。6个生产队的分布大体上是这样的:北道街人口多,从东往西分为4个队;东半部多黄姓,基本上是一队和二队;西半部多李姓,大体上为四队和五队。南道街住户较少,大体上是从中间分开,东半部为三队,西半部为六队。
在集体生产的背景下,这种按区域划分生产队的办法,从生产管理的角度看,有一定的合理性,至少每天上工时队长敲钟派活比较方便。但是,也正是这种按区域划分的办法,给三队发展集体经济带来了“先天性”的困难,导致很多年里三队一直是全村的“老末”。
按总人口,当时宋庄大约有550人(1964年第二次全国人口统计是585人),平均一个生产队近100人。但是,划为三队的这一片,区域不小,但居住的家户比较分散,只有20户,81口人。人口少,姓氏倒不少,不仅有李、黄两大姓,还有赵姓和王姓。由于姓氏多,人口少,居住又分散,凝聚力就不强。更要命的是,一个生产队,只有黄本荣、黄本其、李宗祥、赵恒鑫4个青壮年劳力,其余都是老弱妇幼,充其量能算半劳力,也不过七八个。试想想,一百多亩地,百十口人穿衣吃饭,一年四季夏收秋播,都让这么几个人去干,实在是勉为其难。可以说,三队一出生就严重“先天不足”,注定以后难有好日子过。
当时集体生产,一天三上工,都是以队长敲钟为号令,所有劳力在钟下集中等队长派活。眼看其他队的队长把上工钟铛铛一敲,钟下即刻人头攒动,人声鼎沸;待队长派完活,几十号人很快就扛锄拿锨,直奔地里去了。而在三队钟下,却凋凋零零难见几个人影。由于劳力少,好多该干的农活干不过来,队长急得抓耳挠腮也无计可施。
有一年夏季,天气特别热,不仅庄稼长得快,野草也同样疯长,需要尽快除草施肥。队长把钟敲了一遍又一遍,也只有稀稀拉拉几个人来。队长无奈,只好领着仅有的几个人去干活。结果是,那年秋季的玉米一遍都没有锄完。秋天收获时,地里的草有一尺多深,哪能有什么好收成。
1964年开始农业学大寨,各生产队完成收割播种任务后,就开始组织劳力深翻土地。三队劳力少,大宗农活也干不出来,就组织放假的学生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秋收季节,中小学一放假,队长就把黄存敬、赵天中、黄存钦、王永全等几个十三四岁的学生组织起来,让他们拉着平车,背着夹杆,去爬树卸柿子。那一年,柿子丰收,树上果实累累,几个孩童倒也乐此不疲。
柿子卸完以后,开始耕地,准备秋种。当时地里坟头很多,犁地总有一些地方犁不到;还有每块地的横头,也有一些犁不到的地方,队长就派这几个学生用农具去深翻这些犁不到的地方。
因为缺少劳力,老师放假也不得休息。三队有一个老师名叫黄本宽,并不在本村学校教学。虽然五十多岁了,每逢放假在家,就帮助队里干活。他不但有学问,而且性格和善。几个学生一边干活,一边听他讲东周列国、三国、水浒等故事,也不觉得干活累了。
那些年,三队是全村男女老少皆知的“永久牌”尾巴队。1961年年终分配结算,三队每个劳动日值只有0.38元。为了顾点大家的面子,最后是按0.4元结算的。
三队成立后的头几年,老一辈的黄本富、黄本实、黄本其都当过队长,挂过帅。但因为条件差,劳力少,一直困顿不前。
三队有起色,始于1968年。这一年,年过三十的黄存谦接过了队长的担子。他首先开会整顿纪律,分析队里的困难,鼓励大家同心协力奋斗。为了制定生产种植计划,他一连多天在各个地块东奔西跑,揣摩思量,合理安排。两年以后,三队总算止住了颓势,初步有了点起色。
1970年,驻村工作组经过调查走访,认为黄存谦是个人才,就培养他入了党。第二年,黄存谦就当上了大队党支部书记。
党支部书记要负责全村的事,自然不能再管三队的事了。三队让谁接任队长?当然还是要选年轻人。于是,从1970年开始,三队年轻人开始“轮流坐庄”,有干一年的,有干半年的,还有干个把月的,走马灯似的轮换。先后干过队长的,有王永全、黄发魁、黄习会、黄存敬、赵小根、赵钢旗等七八个人。每个人上任时,也都雄心勃勃,甚至可以说是披肝沥胆,但怎奈三队先天不足,无力回天,最后都心灰意冷撂挑不干了。
没人干,怎么办?大队干部开会商量,准备从外队调个人来当三队队长。是否可行?先在三队开会讨论讨论。开会时,开始大家都表示没有异议,同意大队安排。但会议中间,突然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有一个人站了出来,表示坚决不同意!大家循声看去,原来是六十多岁的黄本立。他说:“咱三队大小百把号人,去外队请人当队长,丢不丢人?还有脸走在大街上吗?如果没人当队长,我来干!”老汉一席话,引来大家一片赞许,自然都同意让他干。
黄本立老汉,人很正派,在三队名声也好,大家一向都很尊重他。但是,当队长可不是光会为人处事就行了,几个月下来,老人家累死累活,旧貌依然变不了新颜,也撂挑不干了。
这一下,三队又没有队长了,大队干部只好又到三队召集各户户主开会选队长。这一次,还真选中了一位大多数人看好的年轻人,名叫李东立。李东立当年27岁,风华正茂。他不仅为人和善,吃苦耐劳,且勤奋好学,思维敏捷。对选他当队长这事,他并没有思想准备。所以,一开始他也是死活不愿意干,后来耐不住大家的一再劝说,只好勉强接受了。
李东立当队长,是在刚改革开放不久的1979年。要不是改革开放,大家肯定也不会选他,因为他家是富农成分。在过去几十年里,选一个地富子弟当生产队长,那是不可想象的事。到1979年,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根据有关政策,村里还专门召集地富子女开会,让他们在统一印制的表格上签字,以文字形式确认他们的“人民公社社员”身份。这虽然只是一种形式,但对于地富子女们来说,则是一种政治上的极大慰藉。
李东立当队长时,生产队已经开始实行联产责任制,农田管理已经不需要生产队长多操心了。各队生产队长的主要精力大多放在发展副业创收、提高群众生活水平上。李东立当上队长后,先是小打小闹购置了一台轧面机,派一名妇女管理着。虽然收入不多,但天天能为队里挣几块零花钱,集体花钱就活泛多了。另外,三队的王永全、王永财兄弟俩子承父业,都是杀猪能手,能不能在这方面做点文章?按当时政策,不许个人杀猪卖肉,但允许集体经营。李东立就让他兄弟俩以生产队集体经营的名义,经营杀猪卖肉的生意,兄弟俩每人每天给队里上缴一块五毛钱,记一个工,其余收入归个人所有。这样一来,集体、个人皆大欢喜。
再后来,李东立经过走访大大小小的工厂和形形色色的公司,觉得运输市场特别活跃,可以在运输上做点事。他认为这是个商机,决心赌一把。于是,在集体没钱的情况下,他毅然向信用社贷款7500元,买了一台拖拉机。在当时,7500元可不算个小数目,如果搞砸了,后果不堪设想。为稳妥起见,他让副队长李平安和赵钢旗开拖拉机跑运输,并制定了详细的管理办法。两个人都很积极,除在农忙时服务本生产队外,农闲时就四处奔波拉运输给队里挣钱。结果不到一年,就还完了信用社的7500元贷款,等于一年给生产队挣下了一台拖拉机,一时博得全村人的一致好评。
1977年,济源钢铁厂医院计划从厂内搬迁到厂外,地址选择的是三队的土地,需要五亩地。当时耕地审批很严格,县土地局的权限是一次审批不能超过3亩。为了能在本县得到审批,就得“化整为零”分批办手续,先批2.9亩,用来盖住院部的房子。其余的2.1亩先预留着,用于盖门诊楼,等到第二年再审批。
住院部施工开始后,李东立让人把预留的2.1亩地整理好,买了100多棵小桐树栽上。一年后,2.1亩预留地审批下来了,但地里的桐树也长大了,枝繁叶茂的小树,怎么算价钱?为此,钢厂医院和三队说不到一块儿:钢厂医院只愿出1000多元青苗补助费,三队则要求按成材树付钱,每棵60元。谈了将近一个月谈不成,施工队已经进了工地,亟待开工,钢厂只好按7000元赔付了结此事。
对这事,当时人们说法不一,有说李东立思想活跃三队沾了光的 ,也有人说那么大一个钢铁厂,占了农民5亩地,就等于占了人家5口人的口粮田,多付几千块钱也不算什么。不论怎么说,至少说明李东立是一个会动脑筋的人,三队选李东立当队长是选对了。
几年以后,三队的贫穷状况一步步得到了改变。到1982年分配时,每个劳动日值达到0.85元,赶上了一贯先进的六队。三队终于甩掉了落后帽子,跨入了先进行列。
三队虽然落后多年,但也有亮点,还有趣闻。当年,各生产队都有马车,主要不是服务农业生产,而是用来跑运输,为集体增加收入;说是搞副业,其实是主业,是生产队诸项集体开支、年终分红的主要经济来源。但置办一套马车不容易,买一匹骡子得两千块上下,四匹骡子加上一辆胶轮马车,就相当于生产队的半个家业。三队虽然穷,也得想办法啊,就先买一棵大槐树,请木匠做成车棚,又买了车轱辘,再下来就是贷款买牲口了。拉马车,一般都是用骡子或者是马,再次也得是驴,但驾辕必得是比较高大的骡子,因为马车下坡时,驾辕的骡子是关键。三队穷,不敢花大价钱买辕骡,就花600元买了一头一只瞎眼的骡子。因为是独眼,这骡子拉磨拉水车转圈圈没问题,走直道就会摇摆不定。不过,这还不算最让三队人难堪的。最让他们没面子的,是用一头黄牛拉梢套,显得不伦不类。于是,就有人笑问三队的人:“这到底是马车还是牛车?”
不过,后来也有让三队人长脸的“畜生”,那就是有一头母驴,一连几年为生产队生下了5头小骡驹。几年以后,小骡驹都长大了,一个个膘肥体壮,生龙活虎,套在马车上,威风凛凛,人人艳羡,简直称得上风光无限!这大概也算苍天有眼,不忍心看着三队的二十多户人家一直让人侧目相看,冥冥之中给了他们一点恩泽吧。
下篇 集体财产拍卖记事
1983年3月的一天早饭后,第三生产队的各户社员都按照前一天队长李东立的通知,早早来到饲养处大院开会,商讨生产队处理拍卖财产事宜。
队长还没有到,群众已经来了不少。大家看着满院堆放的农具等物品,议论纷纷。李东立来到后,简要说明了开会的目的:就是按照公社会议的精神,把生产队所有财物拍卖处理,然后把拍卖款给社员按人口分下去。李东立最后说:“队里所有的财物,今天都放在大院里,大家好好看看。”队长说到这里,稍微停顿了一下,只见 50来岁的芦庆兰站了起来说道:“1962年咱们三队成立,当时全队老少75口人,穷得要命;经过这20年,现在队里变好了,怎么又要解散?我心里真不好受!”
李东立听芦庆兰说完,又接着说:“现在确实不错,一个劳动日1块多;今天分队,我心里也难受。但大家要往前看,现在工业化发展很快,以后的日子一定会更好,要相信上级领导。大家既然来了,就要按上级安排,把队里的财产处理好,每样东西我起个价,谁要谁说话;还有想要的就加价,一次递价5毛,谁出的价高归谁。”
院子里堆放的,都是犁耙、铁杈、木杈、扫帚、木锨、喷雾器等小件东西,均是种地打场必须使用的家具,以后分田单干,家家户户也都离不了。由于当时大家已经听说了上面的精神和外村的做法,思想已有所准备了,也就默认了队长的安排。
队长一开始拿起来或指认的东西,大多是1元、2元、5元、8元的物品,喊了拍卖价后,买的人还算比较踊跃;有些东西没扛(音杠)到,也没有很争,因为这些东西收麦前到庙街小满会上都能买到。只是拍到种地用的铁耧时,有人提议:这耧秋后种麦家家户户都得用,但每户用的时间都很有限,一家只用一晌半晌,还不如不要处理,咱们轮流保存,到时大家轮流用,免得到外村去借。这一提议,立即得到大家的赞同。但又有人提出,队里原来是3张耧,现在只有2张,那1张在哪里,难道丢了不成?其实,那1张耧也没有丢,是去年队里种完麦子后,李立庄把耧借给了他丈母家用,用后一直没有退还回来,立庄也忘了。于是,会后就安排李立庄及时转告了亲家。到秋天种麦时,他丈母家就把耧还了回来,也没耽误大家使用。这是后话。
小件农具拍卖完,剩余的大多是“冷货”。队里搞副业时买过一台加工螺丝的设备,现在不用了,就成了一块废铁。队长喊价60元,没人愿意要。停了一会儿,王永财说:“大家都不要,我要。”王永财于是就买了下来。可买回家没停一星期,本村黄居财就找到王永财家,又加价15元,把废铁买走了。王永财算是一转手挣了15元。
还有队里做钉马掌生意时留下的一堆半成品,实际上也是废铁。过磅350斤,队长按废铁价每斤0.36元喊价,也是没人买,最后李立庄买下了。李立庄买走后,一直在家放了两年,废铁价涨到每斤0.46元,立庄算是净挣了35元。
还有一副铁蒸笼,是生产队集体劳动时偶尔做饭用的,有筚有圈,一应俱全,好几个人都想买,队长喊价16元,几个人就一个接一个5毛5毛往上加,转眼就加到了19元,气氛一时显得有点紧张。这时,赵钢其站起来走到蒸笼跟前指着说:“今天不管涨到什么价,我非要不可,我现在报价十九块五”。众人见钢其脸红脖子粗志在必得样子,况且价也涨得不低了,也就没人再争了,算是成全了钢其。现在和钢其说起这件事,他还说当初确实冲动,钱是没少出,但这些年来家里蒸馍用的都是它;每逢过年,蒸年馍还有人来借呢。“已经用了40年了,有了感情,我一点也不后悔。”
当天晌午,院子里堆放的东西差不多都拍卖完了。队长说:“小东西卖完了,大宗的还有打麦机、50拖拉机和房屋、骡子,我说个价,大家回去考虑考虑,三天后还来这里拍卖。这些东西一律要现款,不赊欠,到时谁要买就带钱来!”
三天后,在大院里首先拍卖打麦机。这个打麦机比较先进,队里已经用过几年了,效率很高。队长喊价1300元,王永全说:“谁要谁说话,咱们组织五六家合伙把它买走吧!”很快,黄习会、王永财、郭秋等联合了6家,立刻就买走了。
接下来是卖骡子。当时,各村生产队都在解体,市场行情不是太好,队长定的价都不高,拉马车驾辕的大黑骡只定了700元,被黄本其买走了。黄习会和郭秋也都各买了1匹,不知道后来卖了多少钱,赔挣如何。赵小根买了队里的黑色瞎眼骡,出价250元,委托牛经济黄心英转卖,本想多少赚几个,结果两天后黄心英帮他卖掉了,还是250元,一分钱也没有赚,不过也没赔。
最后,队里还有一头老草(母)驴。说起这头母驴,真不简单。当初,它曾给三队一连生下5头小骡驹,个个都健康成活,给贫困的三队增加了不少收入。生下第5头小骡驹时,队长黄本立说,老驴给队里出大力了,这次让它歇一年,来年再带驹(配种)。谁知歇了一年,以后数年再也怀不上孕了。就是这样,队里也舍不得卖掉,一直闲喂着,大家都把它看成是队里的“功臣”;眼下看着生产队要解散了,没法再养下去了,队长也只好忍痛割爱,以150元低价便宜卖掉了。
下面轮到卖50拖拉机了。拖拉机是队里花14000多元买的,生产队使用还不足两年,队长喊价9000元,够便宜了,可是说来说去却没人愿意要。最后,有些人就鼓励赵钢其买。可赵钢其一直摇头,不愿意买。队长见大家都不要,就说:“咱队里人都不愿买,那外边(指外村)有人愿意出9000元要,就让人家开走吧。”这一来,大伙又有人不同意了。黄小战说:“9000元太便宜,本队里人要没说的,外边人想要,坚决不行。”会计王永全说:“咱们自己不要,还不让外边人买,那拖拉机还卖不卖?”众人一时乱嚷嚷起来。忽然,老干部黄本富站起来说,干脆找间房把拖拉机锁起来,等价格高了再卖。这一说,大伙嚷嚷得更厉害:“锁起来?猴年马月才能卖掉,大伙还急等着分钱呢。”最后,还是队长力排众议,让外人出9000元把拖拉机开走了。事后曾有人找过赵钢其,问他那么便宜的事儿你为什么不干?他说:“还不是没钱,别说9000元,1000元我也拿不出来,找银行贷款也贷不到9000元。如果我能买下,不出10天,就能轻松卖到1万元,没钱难倒英雄汉呀!”
最后是拍卖饲养院的5间草房。房屋木料都不咋样,梁是叉手梁,檩椽也很不像样,全都是柳木,队长定价是1间60元,让大家回家考虑考虑。在此期间,赵发惠联系了思礼砖厂负责人,砖厂派人来看了看,愿意要,打算拆掉后把木料拉回去盖工棚用。三天后,思礼砖厂就派人来到饲养院,按拍卖当天定的价格,出300元买下了5间房。紧接着又派了几个人来,一上午就把5间房拆得一干二净,用拖拉机把木料全部拉走了。事后,砖厂给了赵发惠80元辛苦费。
本来天天人欢马叫的饲养处大院,几天之内就大变样了:先是显得一片空空荡荡,继而又变得狼藉不堪了!
三队拍卖财产一共拍了多少钱?因时过境迁,当事人大多已经记忆模糊,难以说清了。经过调查走访,仅得如下信息:1. 当时三队没有外债,因为队长李东立生前曾说过,1981年买拖拉机时集体贷款7500元,一年后就用拖拉机搞运输挣的钱还清了这笔贷款。2.各生产队拍卖财产结束后,大队设了一个联队会计(会计员李守安),让各生产队统一在联队会计处存了一笔款,其目的是以防日后集体用钱再叫社员摊派。数量虽然不知几何,但据赵天中的记忆,三四年后,联队会计撤销,他家还分了十几元钱。他家当时6口人。如此算来,联队会计处那笔存款有三四百元。3.会计王永全认为,当年三队的经济状况还是比较好的,各家肯定分有钱,一个人分了150元上下。但其妻却坚持说没有分过钱,因为她家当年有6口人,如果一次分了千把块,不会忘记。4.当年三队拍卖财产变现的收入,有两万元上下。在当时生产队纷纷解体、拍卖财产收入十分明朗的情况下,这笔款很难流失。综合分析,三队集体财产拍卖后,应该按人口分过一笔款,数量不会少于每人100元。拿当年的工薪阶层月工资40元作比照,也算一笔不菲的进项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