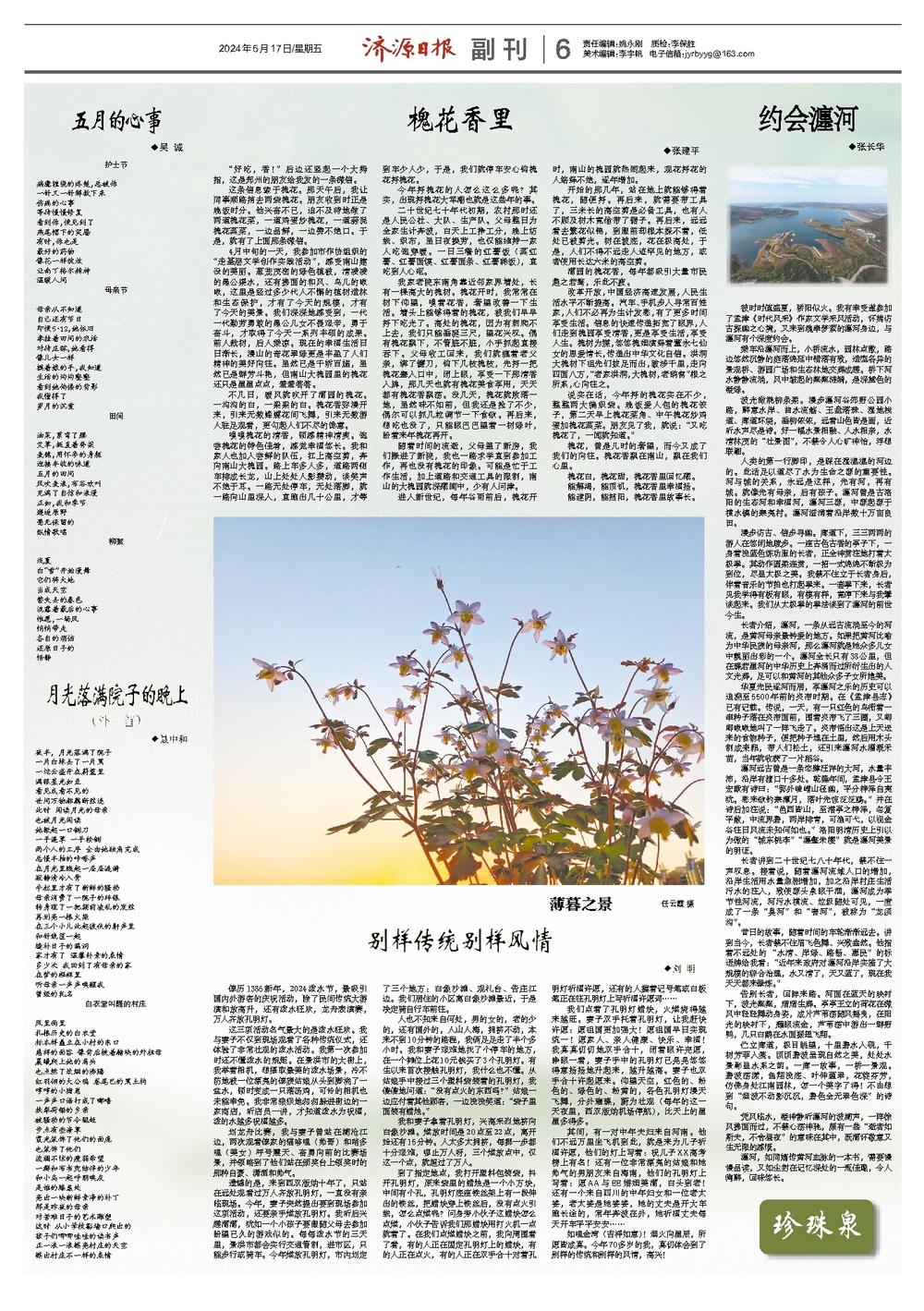“好吃,香!”后边还竖起一个大拇指,这是郑州的朋友给我发的一条微信。
这条信息缘于槐花。那天午后,我让同事顺路捎去两袋槐花。朋友收到时正是晚饭时分。他兴奋不已,迫不及待地做了两道槐花菜,一道鸡蛋炒槐花,一道蒜泥槐花蒸菜,一边品鲜,一边赞不绝口。于是,就有了上面那条微信。
4月中旬的一天,我参加市作协组织的“走基层文学创作实践活动”,感受南山建设的美丽。葱茏茂密的绿色植被,清凌凌的愚公渠水,还有拂面的和风、鸟儿的啾啾,这里是经过多少代人不懈的植树造林和生态保护,才有了今天的规模,才有了今天的美景。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一代一代勤劳勇敢的愚公儿女不畏艰辛,勇于奋斗,才取得了今天一系列丰硕的成果。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现在的幸福生活日日渐长,漫山的奇花翠绿更是丰盈了人们精神的美好向往。虽然已是千娇百媚,虽然已是群芳斗艳,但南山大槐园里的槐花还只是星星点点,羞羞答答。
不几日,暖风就吹开了满园的槐花。一沟沟的白,一梁梁的白。槐花香弥漫开来,引来无数蜂蝶花间飞舞,引来无数游人驻足观看,更勾起人们不尽的馋意。
嗅嗅槐花的清香,顿感精神清爽。饱尝槐花的特色佳肴,感觉幸福悠长。我和家人也加入尝鲜的队伍,扛上高空剪,奔向南山大槐园。路上车多人多,道路两侧车排成长龙,山上处处人影攒动,谈笑声不绝于耳。一路无处停车,无处落脚,就一路向山里深入,直跑出几十公里,才等到车少人少,于是,我们就停车安心钩槐花捋槐花。
今年捋槐花的人怎么这么多呢?其实,出现捋槐花大军潮也就是这些年的事。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农村那时还是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父母整日为全家生计奔波,白天上工挣工分,晚上纺线、织布,虽日夜操劳,也仅能维持一家人吃饱穿暖。一日三餐的红薯饭(蒸红薯、红薯面馍、红薯面条、红薯稀饭),直吃到人心呕。
我家老院东南角靠近邻家界墙处,长有一棵高大的槐树。槐花开时,我常常在树下仰望,嗅着花香,奢望改善一下生活。墙头上能够得着的槐花,被我们早早捋下吃光了。高处的槐花,因为有刺爬不上去,我们只能垂涎三尺,望花兴叹。偶有槐花飘下,不管脏不脏,小手抓起直接吞下。父母收工回来,我们就缠着老父亲,绑了镰刀,钩下几枝槐枝,先捋一把槐花塞入口中,闭上眼,享受一下那清香入脾,那几天也就有槐花美食享用,天天都有槐花香飘荡。没几天,槐花就败落一地,虽然味不如前,但我还是捡了不少,偶尔可以抓几粒调节一下食欲。再后来,想吃也没了,只能眼巴巴望着一树绿叶,盼着来年槐花再开。
随着时间的流逝,父母盖了新房,我们搬进了新院,我也一路求学直到参加工作,再也没有槐花的印象。可能是忙于工作生活,加上道路和交通工具的限制,南山的大槐园就深藏闺中,少有人问津。
进入新世纪,每年谷雨前后,槐花开时,南山的槐园就热闹起来,观花捋花的人络绎不绝,逐年增加。
开始的那几年,站在地上就能够得着槐花,随便捋。再后来,就需要带工具了,三米长的高空剪是必备工具,也有人不顾及树木竟偷带了锯子。再后来,远远看去繁花似锦,到跟前却根本探不着,低处已被剪光。树在坡底,花在极高处,于是,人们不得不远走人迹罕见的地方,或者使用长达六米的高空剪。
满园的槐花香,每年都吸引大量市民趋之若鹜,乐此不疲。
改革开放,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汽车、手机步入寻常百姓家,人们不必再为生计发愁,有了更多时间享受生活。信息的快速传递拓宽了眼界,人们走到槐园享受清香,更是享受生活,享受人生。槐树为媒,悠悠槐姻演绎着董永七仙女的恩爱情长,传递出中华文化自信。洪洞大槐树下祖先们拔足而出,跋涉千里,走向四面八方,“老家洪洞,大槐树,老鸹窝”根之所系,心向往之。
说实在话,今年捋的槐花实在不少,整整两大编织袋。晚饭爱人包的槐花饺子,第二天早上槐花菜角、中午槐花炒鸡蛋加槐花蒸菜。朋友见了我,就说:“又吃槐花了,一闻就知道。”
槐花,曾是儿时的奢望,而今又成了我们的向往。槐花香飘在南山,飘在我们心里。
槐花白,槐花甜,槐花香里回忆藏。
能解渴,能顶饥,槐花香里幸福扬。
能遮阴,能挡阳,槐花香里故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