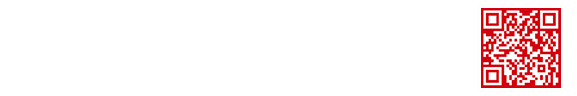从隋唐到明清的1300年间,科举时代的人才选拔标准,经历了一个从“不唯分数”到“唯分数”的演变过程。唐代进士科实行“通榜”和“公荐”制度,当时录取进士不仅看考场成绩,还“采誉望”,即参考平时的才学水平和诗文名声,参考达官贵人和著名人士的推荐,用现在的说法就是“综合评价、多元录取”。其优点是确有主考官录取了许多社会上公认的高水平才士。如唐贞元八年(公元792年)的“龙虎榜”,就出了韩愈、欧阳詹等名士和多位后来成为宰相的著名人物;其局限是主管进士科举的考官自由裁量权过大,是否公平客观往往取决于“知贡举”者的眼光和操守;其弊端是可能出现世家大族干预录取,不够公平客观的现象,导致一些有才华的寒士落选。
自从北宋科举普遍实行糊名、誊录制度以后,完全不参考举子平时的声望、水平和作品,科场“一切以程文定去留”。“程文”即考场上的答卷,就是只凭考场上表现出来的水平和成绩来录取,即“唯分数”选才。科举考试这一选才制度,在创立之初引起相当多的争论。北宋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疏》里论说,州郡发解试应“必先考其履行,然后取以艺业”;而采用糊名、誊录制度后,考生“不见姓字”,对其日常行为举止更是无从考究。因而范仲淹建议重修发解试条例,加入对举子德行履历的考察,并主张废除糊名、誊录制度,考察“履行无恶、艺业及第”者方可录取。次年(公元1044年),包拯反对废止糊名、誊录制度时指出,一个人的实际德行很难核实,何况考官未必都能以公心取人:“或缘其雅素,或牵于爱憎,或迫于势要,或通于贿赂,势不得已,因而升黜者有矣,又何暇论材艺、较履行哉?”可见,当时包拯对维护公平的糊名、誊录制度持肯定态度。
北宋政坛对于糊名、誊录制度的争论,实质上是对科举取士标准和考核内容的商榷,反映了部分大臣对科举取士“唯分数”与“兼顾德行”的不同意见。
北宋中期,关于是否“唯分数”取人的争论还延伸到科举存废的问题。针对有人提出应恢复察举、实行全面考察德行的办法,苏轼在《议学校贡举状》中极力为科举辩护,认为科举考试有一定标准,远远优于无客观标准的察举德行,因为察举制主要考核德行,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只能通过举子的言行考察。但这一考察很难全面,且德行考核被赋予功利性时,容易促使举子迎合上意,弄虚作假。在苏轼看来,主张废除科举、恢复察举者,只看到了考察德行的优势,却忽视了这一制度的可操作性,因而他坚定地站在具有客观标准、“唯分数”取士的科举制一方。
由于苏轼的反驳有理有据,故没有人再直接进行辩驳。 (《今晚报》 狄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