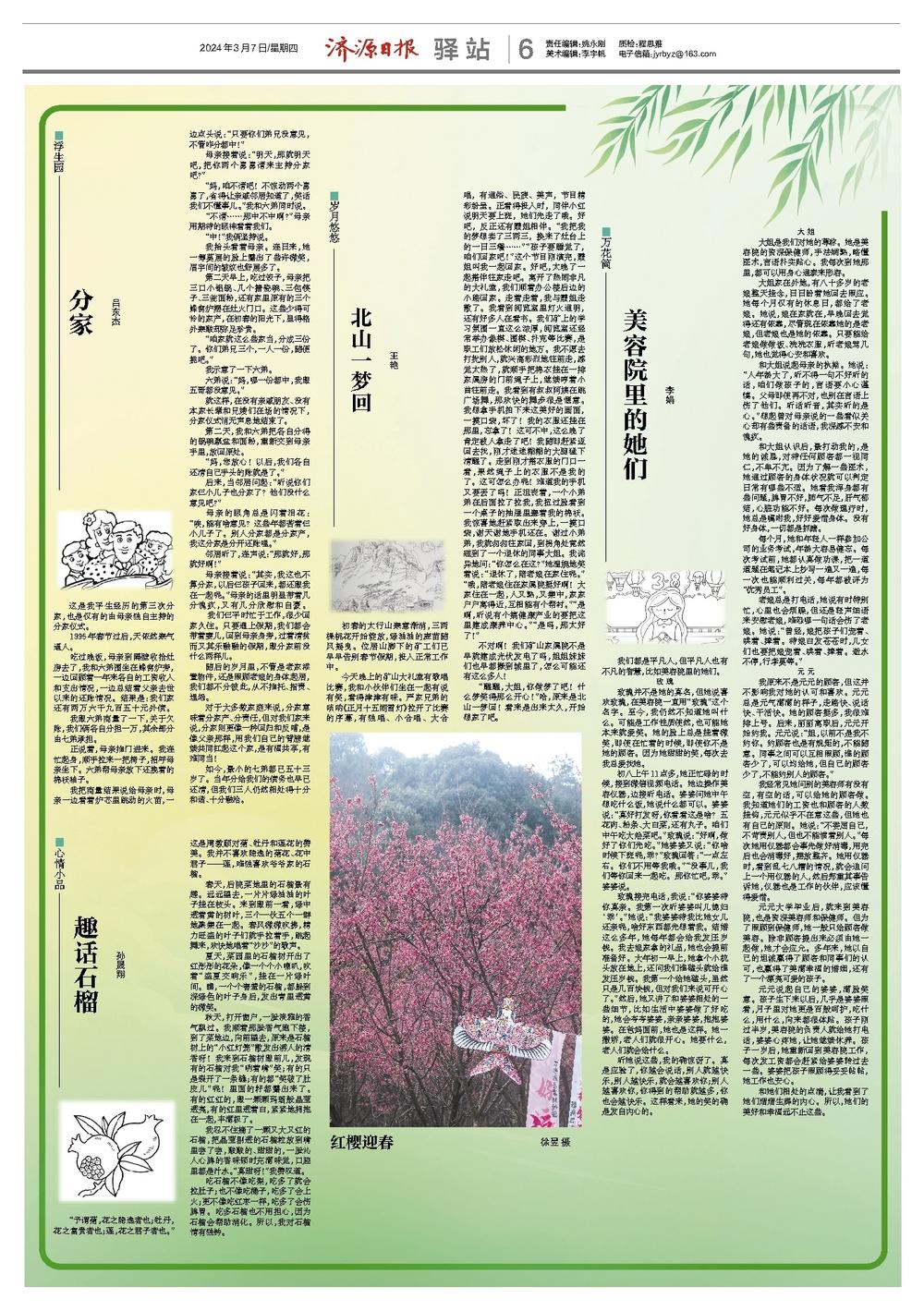这是我平生经历的第三次分家,也是仅有的由母亲独自主持的分家仪式。
1995年春节过后,天依然寒气逼人。
吃过晚饭,母亲到隔壁收拾灶房去了,我和六弟围坐在蜂窝炉旁,一边回顾着一年来各自的工资收入和支出情况,一边总结着父亲去世以来的还账情况。结果是:我们家还有两万六千九百五十元外债。
我跟六弟商量了一下,关于欠账,我们俩各自分担一万,其余部分由七弟承担。
正说着,母亲推门进来。我连忙起身,顺手拉来一把椅子,招呼母亲坐下。六弟帮母亲放下还挽着的棉袄袖子。
我把商量结果说给母亲时,母亲一边看着炉芯里跳动的火苗,一边点头说:“只要你们弟兄没意见,不管咋分都中!”
母亲接着说:“明天,那就明天吧,把你两个舅舅请来主持分家吧?”
“妈,咱不请吧!不惊动两个舅舅了,省得让亲戚邻居知道了,笑话我们不懂事儿。”我和六弟同时说。
“不请……那中不中啊?”母亲用期待的眼神看着我们。
“中!”我俩坚持说。
我抬头看着母亲。连日来,她一筹莫展的脸上露出了些许微笑,眉宇间的皱纹也舒展多了。
第二天早上,吃过饺子,母亲把三口小铝锅、几个搪瓷碗、三包筷子、三瓮面粉,还有家里原有的三个蜂窝炉摆在灶火门口。这些少得可怜的家产,在初春的阳光下,显得格外寒酸却弥足珍贵。
“咱家就这么些家当,分成三份了。你们弟兄三个,一人一份,随便挑吧。”
我示意了一下六弟。 六弟说:“妈,哪一份都中,我跟五哥都没意见。”
就这样,在没有亲戚朋友、没有本家长辈和兄嫂们在场的情况下,分家仪式悄无声息地结束了。
第二天,我和六弟把各自分得的锅碗瓢盆和面粉,重新交到母亲手里,放回原处。
“妈,您放心!以后,我们各自还清自己手头的账就是了。”
后来,当邻居问起:“听说你们家仨小儿子也分家了?他们没什么意见吧?”
母亲的眼角总是闪着泪花:“唉,能有啥意见?这些年都苦着仨小儿子了。别人分家都是分家产,我这分家是分开还账哩。”
邻居听了,连声说:“那就好,那就好啊!”
母亲接着说:“其实,我这也不算分家,以后仨孩子回来,都还跟我在一起呢。”母亲的话里明显带着几分愧疚,又有几分欣慰和自豪。
我们仨平时忙于工作,很少回家久住。只要遇上假期,我们都会带着妻儿,回到母亲身旁,过着清贫而又其乐融融的假期,跟分家前没什么两样儿。
随后的岁月里,不管是老家添置物件,还是照顾老娘的身体起居,我们都不分彼此,从不推托、指责、埋怨。
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分家意味着分家产、分责任,但对我们家来说,分家则更像一种回归和反哺,是像父亲那样,用我们自己的臂膀继续共同扛起这个家,是有福共享,有难同当!
如今,最小的七弟都已五十三岁了。当年分给我们的债务也早已还清,但我们三人仍然相处得十分和谐、十分融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