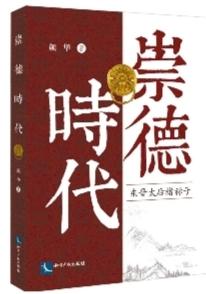(接上期)
4
褚蒜子光芒覆盖的时代,除了与北方的割据力量较量,也可以说是她与桓温既惺惺相惜又斗智斗勇的时代。
《世说新语·品藻》多述及魏晋名士玄学清谈,记录了清谈风气熏陶下而呈现的各种机巧言论。其中,就讲到了桓温的故事——桓公少与殷侯齐名,常有竞心。桓问殷:“卿何如我?”殷云:“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
最后这句话,成了这个历史典故中的名句,后世使用频率极高。如辛弃疾就多次在其词中化用这句话——“宁作我,岂其卿”“翁比渠侬人谁好?是我常、与我周旋久。宁作我,一杯酒”等,都抒发了词人辛弃疾追求真我、独立不阿,不屈志附人、不丧失自我的决心和气概。
在作家颜华笔下,有大量的笔墨写到桓温与殷浩的斗智斗勇,写到朝廷与大臣的斗智斗勇。桓温年轻时就与殷浩齐名,所以常常有攀比、竞争之心。桓温问殷浩:“你和我相比,谁强些?”殷浩回答说:“我已经和自己打交道很久了,宁愿作我!”这几句简单的对话后边,其实有着长长的历史背景。
桓温和殷浩从小一块儿长大,桓温是忠良桓彝之后,为人豪爽,勇猛威武,是晋明帝的驸马。朝廷封他为徐州刺史,都督青、徐、兖三州诸军事。庾翼病逝后,他又出镇荆州,都督六州诸军事,彻底掌握了东晋在长江上游的兵权。
殷浩善清谈玄理,识度清远,少有美名,尤受当时辩士推崇。殷浩隐居十年,待价而沽。时人皆以为其“奇货可居”,堪比管仲、诸葛,甚则有“深源(殷浩的字)不起,当如苍生何”。受当时辅政大臣司马昱推荐,褚蒜子应允,殷浩出仕。殷浩声望极高,又能让朝臣钦服,被朝廷视为股肱之臣。
殷浩代表文臣和朝廷的力量,桓温代表武将和地方的力量,两种力量形成了一种相对的平衡。但世事无常。347年,桓温溯江而上,消灭了成汉政权,权势声望变得空前强盛,朝廷对他也甚是忌惮。为抑制桓温,朝廷就支持殷浩与桓温抗衡。于是,桓、殷这两个从小的朋友,就变成了一时瑜亮,彼此对立。
349年,北方敌对势力后赵皇帝石虎病死,桓温请求北伐,并做好了出兵的准备。但是,桓温此前在自己治地自行募兵、调粮,已引起朝廷对他“不臣之心”的猜忌。朝廷不理桓温出兵请求,而派外戚褚裒北伐,结果失败而归,褚裒也羞愧而死。
350年,冉闵称帝,与后赵分庭抗礼,北方形势更乱。桓温再次请求北伐,屡次上表,但朝廷内部意见不一。王羲之等向太后建议“殷浩的才能在朝堂,在朝堂可谓首脑,让他带兵打仗,实乃弃其长而扬其短”,司马昱等却力挺殷浩,太后最后支持了司马昱。朝廷错误地把北伐的任务交给了长于纸上谈兵的一介文臣殷浩。此后几年,殷浩数次北伐,但都屡战屡败,军粮器械也消耗殆尽。
桓温利用群臣怨恨,上疏严厉指责殷浩的失败,陈列其罪状,要求贬斥。司马昱迫不得已,将殷浩废为平民,并加以流放。从此以后,整个朝廷,桓温大权独揽,再也无人能与之抗衡,东晋历史进入了桓温北伐的时代。
此时,桓温正处于人生顶峰,志得意满;而殷浩则是从顶峰跌落到谷底的一介草民。这则《世说新语·品藻》中的对话,便发生在这个时候。这显然是一个二难选择。“我不如卿”——虽然明哲保身,却显得卑躬屈膝;“卿不如我”——虽然保住了面子,却无异于自毁长城。而一句“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却独辟蹊径,巧妙地绕开了桓温预先设好的“陷阱”,无疑是最好的回答。
但历史向来是成者为王败者寇,任凭你伶牙俐齿又如何?其实,历史上真实的桓温并非小肚鸡肠的一介武夫。他曾在殷浩遭贬后,在众人的嫌弃中,试图再次启用殷浩,但却阴差阳错。桓温曾多次建议太后,如果想富国强民、恢复中原,就要改掉门阀士族世袭制,改革九品中正制,广纳人才,等等,也甚为太后赏识。
但褚蒜子毕竟站在权力的巅峰,面对的是整个国家、整个时局。她欣赏桓温、安抚桓温,肯定其铁骨铮铮之言,但驾驭整个国家的褚蒜子,面对积弊甚深的社会,只能是权衡利弊,等待时机。桓温深知褚蒜子的知遇之恩,对太后的大格局、大智慧甚是钦佩,“暗对自己说,无论如何都要和太后褚蒜子站在一起,帮着她把国家治理好”。
如果圣明的褚太后一直当政,如果以后的几任皇帝也有太后的雄才大略,至少别太窝囊,如果不是朝廷内部的龌龊屡屡耽误了北伐的时机,我想桓温或许就不会生起“取而代之”之心。
5
褚蒜子在那个动荡的时代,无疑是那个时代的定盘星。她为了稳定风雨飘摇的政权,进行了各种强国富民的尝试,比如发展蚕桑经济,比如筹划政治改革,比如引导国民信仰,比如兴办学校、启蒙民智,比如开展对外贸易,等等,无疑都是积极的,正确的。但最终为什么仍然不能走向统一,改变不了内部的叛乱倾轧?这是读完颜华《崇德时代——东晋太后褚蒜子》之后需要深思的问题。
一个国家富有和强大的密码究竟是什么?《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对此有比较深入的论述,我深以为然。一个国家是依赖于社会、政治、经济等的一套运行规则即制度而强大?还是依靠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呢?究竟哪一个才是根本,才是可持续的呢?譬如两个地域毗邻、自然环境十分相似的国家,又曾经统一于一国之下,后分属不同的社会制度,结果几十年下来,两个曾经相同的国家却贫富殊异。在几乎没有地理差异的情况下,制度的差别确实能够带来国家财富的巨大差异,制度因素似乎是至关紧要的。
通常意义上,好的制度应该是在国家层面能够实现财富积累,在个人层面能够激励个人努力创造财富吧。在当下语境中,那些积极强调政府效能、有效控制通货膨胀、提供均等教育机会、保障契约有效执行、打破贸易壁垒、激励资本投资、畅通资本流动、打击职务腐败、保护私有产权等的制度应该都是好的制度吧。拥有良好制度的国家,往往会变成富裕国家,不具备良好制度的国家,往往会变得贫穷。
诚然如是。但是,制度因素也只可以解释部分结果,并不能解释全部。它不是完整的解释,除了良好制度,还有其他因素影响国家财富,比如地理因素。人的地理观往往决定了人的世界观。
偏安江南的东晋王朝,如果在100余年的时间内仍未能光复失地、入主中原,完成国家的统一,那么很可能就会倦怠下去,从此失去了信念,“此处乐,不思蜀”。当时的一些士族门阀很多是反对战争的,认为土地城池并非哪一个国家所固有,失去就失去了,不要因此而争夺,让国家永无宁日。
《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说,“人类各族群的历史循着不同的轨迹开展,那是环境而非生物差异造成的”,意即世界各大陆国家地理环境的差异,最终导致了现代世界各个民族间巨大的发展差异,地理环境决定因素客观存在。英国地理学家、地缘政治学家詹姆斯·费尔格里夫在《地理与世界霸权》中,总结了从原始人出现到工业革命后的人类文明史,基于热量和水的分布,认为温带地区是诞生文明的沃土,诠释了造成不同文明之间发展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地理环境的不同。
我们研究历史终究是为了洞明现实,历史并不仅仅是过去时,而是进行时。历史总是在重复,在今天发生的,到明天它也会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而且我们重复的是以往的历史,也就是说当下正是以往历史重复的过程。今日之事,明或再有;太阳之下,并无新事。读颜华的《崇德时代——东晋太后褚蒜子》,也让我联系到英国人詹姆斯·费尔格里夫的《地理与世界霸权》,联系到美国人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等书籍。
6
褚蒜子固然是那个时代最为耀眼的一颗明星,但她的耀眼或许是因为那个时代太黯淡了,因为时代的黯淡,才显得她明亮?在她主政的几十年里,本来是有望收复北土,完成大一统的。如果她锐意改革,确立一个相对好的社会制度,如果她发现皇帝无能,就像武则天那样取而代之……
但那样的时代,对一个女人,她的作为已难能可贵。过多的假设,就是苛求。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