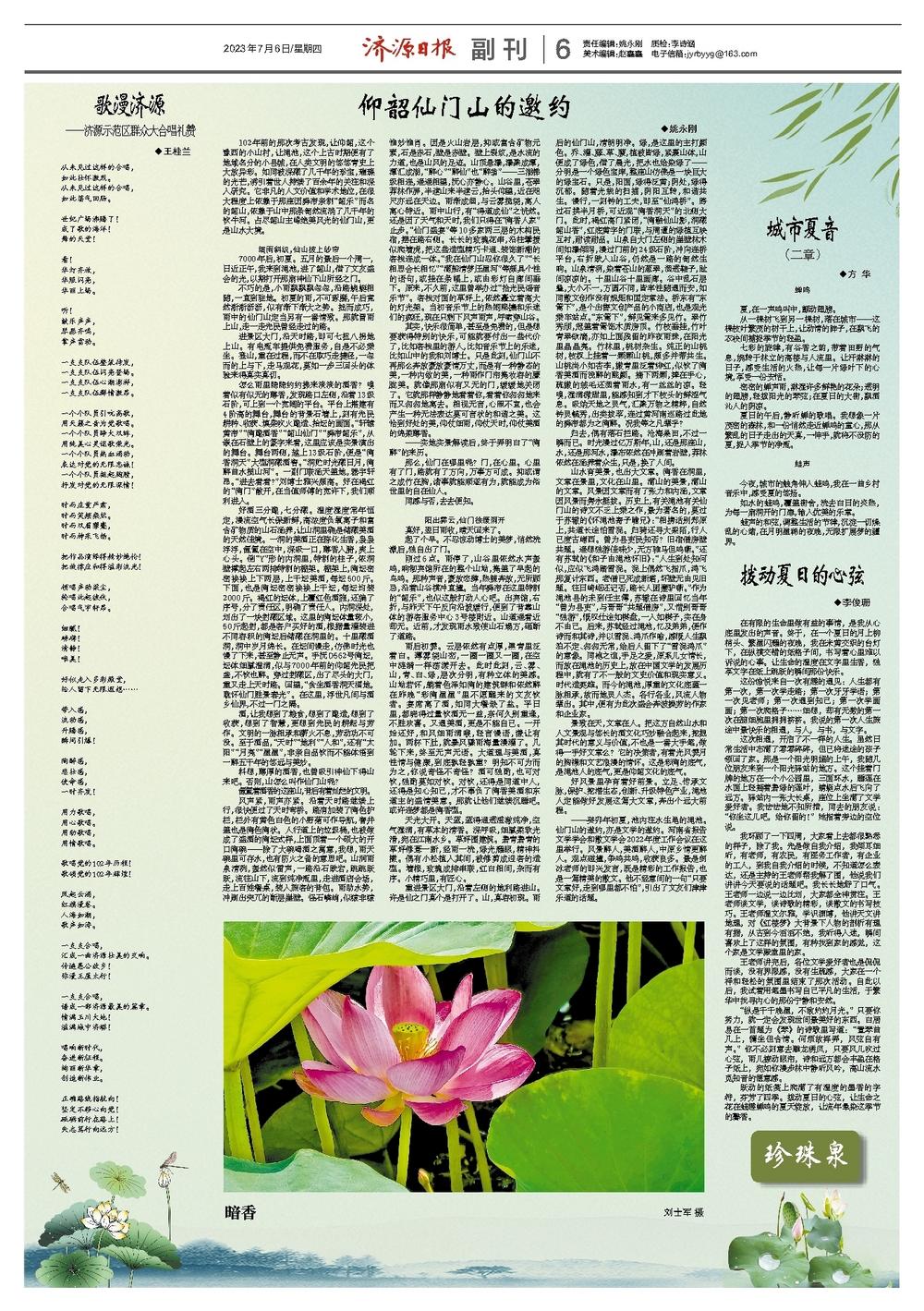102年前的那次考古发现,让仰韶,这个豫西的小山村,让渑池,这个上古时期便有了地域名分的小县城,在人类文明的悠悠青史上大放异彩。如同被深藏了几千年的珍宝,璀璨的光芒,诱引着世人持续了百余年的关注和深入研究。它非凡的人文价值和学术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那座因舜帝亲制“韶乐”而名的韶山,依赖于山中那条訇然流淌了几千年的饮牛河。占尽韶山主峰绝美风光的仙门山,更是山水大境。
细雨斜织,仙山披上纱帘
7000年后,初夏。五月的最后一个周一,日近正午,我来到渑池,进了韶山,借了文友盛会的光,以期打开那扇神仙下山所经之门。
不巧的是,小雨飘飘飘忽忽,沿路蜿蜒相随,一直到驻地。初夏的雨,不可琢磨,午后竟然淅淅沥沥,似有渐下渐大之势。拙而成巧,雨中的仙门山定当另有一番情致。那就冒雨上山,走一走先民曾经走过的路。
进景区大门,沿天时路,即可七扭八拐地上山。有电瓶车提供免费服务,自是不必乘坐。登山,重在过程,而不在取巧走捷径,一忽而的上与下,走马观花,莫如一步三回头的体验来得真实真切。
怎么雨里隐隐约约拂来淡淡的酒香?嗅着似有似无的醇香,发现路口左侧,沿着13级石阶,可上到一个宽阔的平台。平台上搭建有4阶高的舞台,舞台的背景石墙上,刻有先民耕种、收获、填柴吹火酿造、抬坛的画面。“轩辕黄帝”“陶酿酒香”“韶山仙门”“舜帝韶乐”,从嵌在石壁上的篆字来看,这里应该是实景演出的舞台。舞台两侧,越上13级石阶,便是“陶香洞天”大型洞藏酒窖。“洞贮时光藏日月,陶醉曲水揽山河”。一副门联涵天盖地,器宇轩昂。“进去看看?”刘博士雅兴颇高。好在褐红的“陶门”敞开,在当值师傅的宽许下,我们顺利进入。
好酒三分酿,七分藏。温度湿度常年恒定,漫流空气长保新鲜,高浓度负氧离子和富含矿物质的山石涵养,让山洞里确是储藏美酒的天然佳境。一洞的美酒正在陈化生香,袅袅浮浮,氤氲在空中,深吸一口,醇香入腑,爽上心头。倒“Y”形的内洞里,特制的柱子,依洞壁撑起左右两排特制的棚架。棚架上,陶坛密密挨挨上下两层,上千坛美酒,每坛500斤。下面,也是陶坛密密挨挨上千坛,每坛均装2000斤。褐红的坛体,上覆红色酒旌,还编了序号,分了责任区,明确了责任人。内洞深处,划出了一块封藏区域。这里的陶坛体量较小,50斤起封,都是客户买好的酒,根据量灌装进不同容积的陶坛后储藏在洞里的。十里藏酒洞,洞中岁月绵长。在坛间慢走,仿佛时光也慢了下来,甚至静止无声。手抚D562号陶坛,坛体细腻温润,似与7000年前的仰韶先民把盏,不饮也醉。穿过封藏区,出了尽头的大门,重又走上天时路。回望,“贪坐酒香洞天福地,耽怀仙门胜景春光”。在这里,浮世凡间与酒乡仙界,不过一门之隔。
酒,让我想到了粮食,想到了酿造,想到了收获,想到了智慧,更想到先民的耕耘与劳作。文明的一脉相承和薪火不息,劳动功不可没。至于酒品,“天时”“地利”“人和”,还有“太阳”“月亮”“星星”,非亲自品饮而不能体悟到一醉五千年的悠远与美妙。
料想,醇厚的酒香,也曾吸引神仙下得山来吧。否则,山怎么叫作仙门山呢?
氤氲着酒香的这座山,背后有着灿烂的文明。
风声紧,雨声亦紧。沿着天时路继续上行,很快便过了天时弯桥。路肩加装了陶色护栏,栏外有黄色白色的小野菊可作导航,窨井盖也是陶色陶状。人行道上的垃圾桶,也被做成了盛酒的陶坛式样,上面顶着一个硕大的开口陶碗——除了大碗喝酒之寓意,我想,雨天碗里可存水,也有防火之备的意思吧。山涧雨泉清冽,轰然似雷声,一路沿石跌宕,跳跳跃跃,流往山下,流到纯净瓶里,走进酒店会场,走上百姓餐桌,装入旅客的背包。雨助水势,冲刷出突兀的断层崖壁。怪石嶙峋,似猿非猿惟妙惟肖。因是火山岩层,抑或富含矿物元素,石是赤石,壁是赤壁。壁上裂纹,是水流的力道,也是山风的足迹。山顶悬瀑,瀑聚成潭,潭汇成湖,“醉心”“醉仙”也“醉翁”——三湖梯级相连,遥遥相望,抚心亦静心。山谷里,苍翠莽林作屏,半遮山来半遮云,抬头仰望,近在咫尺亦远在天边。雨渐成烟,与云雾搅绕,离人离心特近。雨中山行,有“得道成仙”之恍然。还是因了天气和天时,我们只得在“陶香人家”止步。“仙门盛宴”等10多家两三层的木构民宿,摆在路右侧。长长的玫瑰花串,沿柱攀援似爬墙虎,把这些造型精巧卡通、装饰新潮的客栈连成一体。“我在仙门山忍你很久了”“长相思会长相忆”“满船清梦压星河”等颇具个性的语句,或挂在条幅上,或由彩灯自廊间垂下。原来,不久前,这里曾举办过“拾光民谣音乐节”。客栈对面的草坪上,依然矗立着高大的灯光架。当初音乐节上的热闹熙攘和乐迷们的疯狂,现在只剩下风声雨声,呼啸穿山谷。
其实,快乐很简单,甚至是免费的,但是想要获得特别的快乐,可能就要付出一些代价了,比如客栈里的游人,比如音乐节上的乐迷,比如山中的我和刘博士。只是此刻,仙门山不再那么奔放豪放豪情万丈,而是有一种静态的美,一种内敛的美,一种雨作门帘掩妆容的朦胧美。就像那扇似有又无的门,缓缓地关闭了。它就那样静静地看着你,看着你匆匆地来而又匆匆地离去。相视无言,心照不宣,也会产生一种无法表达莫可言状的和谐之美。这恰到好处的美,仰仗细雨,仰仗天时,仰仗美酒的绵柔醇香。
——实地实景解读后,终于弄明白了“陶醉”的来历。
那么,仙门在哪里呢?门,在心里。心里有了门,路就有了方向,万事方可成。抑或谓之成竹在胸,诸事就能顺遂有为,就能成为俗世里的自在仙人。
同感与否,去去便知。
阳出霁云,仙门徐缓洞开
真好,翌日雨收,晴天回来了。
起了个早。不忍惊动博士的美梦,悄然洗漱后,独自出了门。
刚过6点。雨停了,山谷里依然水声轰鸣,响彻宾馆所在的整个山坳,掩盖了早起的鸟鸣。那种声音,豪放恣肆,热辣奔放,无所顾忌,沿着山谷横冲直撞。当年舜帝在这里特制的“韶乐”,也似这般打动人心吧。出宾馆,右折,与昨天下午反向沿坡缓行,便到了背靠山体的游客服务中心3号楼附近。山道遥看近却无。近前,才发现雨水致使山石塌方,砸断了道路。
雨后初霁。云层依然有点厚,黑青里泛着白。薄雾绕山峦,一圈一圈又一圈,在空中涟漪一样荡漾开去。此时此刻,云、雾、山,青、白、绿,层次分明,有种立体的美感。山坳若怀,躺着色泽如陶的建筑群和依然醉在昨晚“彩陶星星”里不愿醒来的文友饮者。宴席离了酒,如同大餐缺了盐。平日里,都晓得过量饮酒无一益,奈何久别重逢,不胜欢喜。又遇美酒,更是不能自已。一开始还好,和风细雨润喉,轻言慢语,谦让有加。两杯下肚,就暴风骤雨海量漫灌了。几轮下来,终至无声无语。大道理与美酒,真性情与健康,到底孰轻孰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你说奇怪不奇怪?酒可独酌,也可对饮,独酌莫如对饮。对饮,还得是同道中人,还得是知心知己,才不辜负了陶香美酒和东道主的盛情美意。那就让他们继续沉睡吧。或许连梦都是陶香型。
天光大开。天蓝,蓝得通透澄澈纯净,空气湿润,有草本的清香。深呼吸,细腻柔软光滑,宛在江南水乡。草坪围建筑。碧青碧青的草坪修葺一新,经雨一洗,绿光耀眼,精神抖擞。偶有小松植入其间,被修剪成迎客的造型。墙根,玫瑰成排串联,红白相间,杂而有序。小精巧里,有匠心。
重进景区大门,沿着左侧的地利路进山。许是仙之门真个是打开了。山,真容初现。雨后的仙门山,清朗明净。绿,是这里的主打颜色。乔、灌、藤、草、蕨,植被皆绿,紧裹山体,山便成了绿色,借了晨光,把水也给染绿了——分明是一个绿色宝库,整座山仿佛是一块巨大的绿宝石。只是,阳面,绿得泛黄;阴处,绿得沉郁。随着光线的扫描,阴阳互转,和谐共生。慢行,一刻钟的工夫,即至“仙鸿桥”。跨过石拱半月桥,可近观“陶香洞天”的北侧大门。此时,褐红高门紧闭,“陶融仙山影,洞藏韶山香”,红底黄字的门联,与周遭的绿植互映互衬,耐读耐品。山泉自大门左侧的崖壁林木间如瀑倾泻,漫过门前的24级石阶,冲向连桥平台,右折跌入山谷,仍然是一路的訇然生响。山泉清洌,染着苍山的葱翠,洇透鞋子,趾间凉凉的。十里山谷十里画廊。谷中乱石层叠,大小不一,方圆不同,皆率性随遇而安,如同散文创作没有规矩和固定章法。桥东有“东篱下”,是个出售文创产品的小商店,也是观光乘车站点。“东篱下”,鲜见篱来多见竹。翠竹秀颀,冠盖着篱饰木质房顶。竹枝垂挂,竹叶青翠欲滴,亦如上面残留的昨夜雨珠,在阳光里晶晶亮。竹林里,桃树杂生。纯正的山桃树,枝杈上挂着一颗颗山桃,颇多并蒂共生。山桃尚小如杏李,嫩青里泛着绯红,似饮了陶香美酒而浅醉的酡颜。摘下两颗,捧在手心,疏嫩的绒毛还洇着雨水,有一丝丝的凉。轻嗅,湿润微甜里,能感知到才下枝头的鲜涩气息。吸纳天地之灵气,汇聚万物之精粹,自然钟灵毓秀,出类拔萃,连过黄河南巡路过此地的舜帝都为之陶醉。况我等之凡辈乎?
归去,偶有落石拦路。沧海桑田,不过一瞬而已。时光漫过亿万斯年,山,还是那座山,水,还是那河水,瀑布依然在冲刷着岩壁,莽林依然在涵养着众生,只是,换了人间。
山水育美景,也出大文章。陶香在洞里,文章在景里,文化在山里。满山的美景,满山的文章。风景因文章而有了张力和内涵,文章因风景而隽永挺拔。历史上,有关渑池有关仙门山的诗文不乏上乘之作,最为著名的,莫过于苏辙的《怀渑池寄子瞻兄》:“相携话别郑原上,共道长途怕雪泥。归骑还寻大梁陌,行人已度古崤西。曾为县吏民知否?旧宿僧房壁共题。遥想独游佳味少,无方骓马但鸣嘶。”还有苏轼的《和子由渑池怀旧》:“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飞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作为渑池县的未到任主簿,苏辙在诗里回忆当年“曾为县吏”,与哥哥“共题僧房”,又惜别哥哥“独游”,慨叹仕途如棋盘,一入如棋子,实在身不由己。后来,苏轼经过渑池,忆及弟弟,便作诗而和其诗,并以雪泥、鸿爪作喻,感慨人生飘泊不定、匆匆无常,给后人留下了“雪泥鸿爪”的意象。同袍之谊,手足之爱,原系儿女情长,而放在渑池的历史上,放在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中,就有了不一般的文史价值和现实意义。时代造英雄。而今的渑池,厚重的文化底蕴一脉相承,故而地灵人杰。各行各业,风流人物辈出。其中,便有为此次盛会奔波操劳的作家和企业家。
景致在天,文章在人。把这方自然山水和人文景观与悠长的酒文化巧妙融合起来,挖掘其时代的意义与价值,不也是一番大手笔,做得一手好文章么?它的决策者,有着光风霁月的胸襟和文艺浪漫的情怀。这是彩陶的底气,是渑池人的底气,更是仰韶文化的底气。
好风景里孕育着好前景。立足、传承文脉,保护、挖潜生态,创新、升级特色产业,渑池人定能做好发展这篇大文章,奔出个远大前程。
——癸卯年初夏,池内注水生黾的渑池。仙门山的邀约,亦是文学的邀约。河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和散文学会2022年度工作会议在这里举行。风景醉人,美酒醉人,中原乡情更醉人。观点碰撞,争鸣共鸣,收获良多。最是剑冰老师的即兴发言,既是精彩的工作报告,也是一篇精美的散文。他不经意间的一句“只要文章好,走到哪里都不怕”,引出了文友们津津乐道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