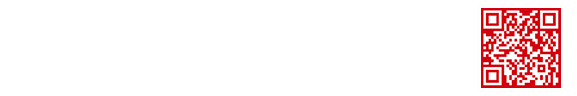《齐迹》这本书的写作,除了我和主人公齐百红之间的关系——同学、同乡、同龄之外,更能引起我创作激情的是齐百红的经历。百红的经历本身已经形成了本书的基本构架,不用虚构,如实写来,就像我们两个人在对话、聊天那样亲切、朴素、自然、真挚,这是一本书的基础。与我其他作品不同的是,字里行间弥漫着一种浓浓的乡情。什么是乡情?乡情是一种永远的记忆,是漂泊、寄居在外的人对故乡山水风物的挂念——村中的老宅还有人居住吗?沟边还有孩童在玩耍吗?窑洞的门口还有燕子在垒窝吗?那些老农具、老手艺还存在吗?那些老槐树、老物件、犁耧锄耙、石凳、石磨、石碾等突然就浮现在脑海里,这种印记是岁月永远也磨灭不掉的!
于是,我心中经常会弥漫着一种深深的惆怅,这种惆怅被我称为乡愁。当我在写作时,常常会想起当年在槐滩(百红老家)的点点滴滴,总有一些零碎的记忆如影随形,挥之不去,比如一缕沁人心脾的槐花馨香,一锅热气腾腾的大烩菜,一个有着悦耳虫鸣的凉爽的夏夜……那种思念和眺望,是只有身处异乡的游子才会有深深的体会和久久的牵萦啊!
乡愁是李白诗中的床前明月,乡愁是鲁迅《故乡》里的少年闰土,乡愁是余光中笔下的海峡邮路,乡愁是席慕蓉心中一棵没有年轮永不老去的树……人,只要心系故乡、情归家园、关注乡村、眷恋自然,便会乡情满满,乡愁漫漫。
于是,《齐迹》就在这浓浓乡情和缕缕乡愁的笼罩下动笔了。
叙事散文是以写人记事为主的散文。这类散文对人和事的叙述、描绘较为具体、突出,同时表现了作者的认知和感受,也带有浓厚的抒情色彩。叙事散文属于纪实文学作品,既然属于非虚构作品,人物、事件、时间、地点都必须是真实的,否则就是小说。我在写《齐迹》的时候,并没有什么想象的东西在作品里面,每一个情节、细节都有原始素材的支撑,都是有出处的,哪怕是一个小小的细节,都是从采访和深入生活中得来的。
在《齐迹》一书中,我重点记述了百红的人格、胸怀、志向等性格形成的内在因素。以百红幼年、青年、中年时期的成长历程为主线,以齐氏家族近百年的家史为辅线,将百红性格形成的“内因”,置于齐氏家族百余年家史的背景之下,通过对齐家的历史变迁,祖辈和父辈的人生经历、性格特征、胆识担当,以及齐氏家族的家规、家训、家教、家风等这些家族文化元素的解析,来阐释这些元素对一个成功企业家的影响、教化、浸染、熏陶,乃至对百红的人生规划、事业追求、胸怀胆魄、为人处世产生的影响、受到的启迪、起到的作用,等等,作为本书的主要内容;并试图将这个家族的历史融入整个民族的历史,将这个家庭和百红成长的经历,置于几十年来国家日益富强的大背景之下,形成一个时代的缩影。
在家族意识日益淡薄的当下,这种以记述一个成功企业家的故土情怀,以一个家庭的家史、家规、家训、家风、家教,对一个企业家的影响为主要内容的作品并不多见,其定位或切入点是否合时宜,我并没有刻意去考究。随性也好,有意为之也罢,只能说,也算一种选择。有道是:文无定法。
在叙事散文中,对人物动作描写的要求,就是要通过人物的动作表现人物的心理。这里就涉及细节典型性的话题。其实,人物的举手投足都是细节,但并不是这些动作都能让读者印象深刻。真正打动人心的细节是具有典型性的,但又是常常被人们所忽略的。细节是刻画人物的有力手段。通过细节刻画人物,才能让人物鲜活有力,性格清晰可见。细节的美,首先在于细节达到了高度逼真的艺术境地。
在《齐迹》中,我曾经选取的一个细节,就是人物的动作刻画。当年(我们读书时的20世纪70年代初)一天午饭时,我和百红都躲在宿舍一角吃“馊窝窝头”。这个细节是我们俩真实的经历。那时,每周日,我们从家里带窝窝头到学校,但是窝窝头只能吃三天。夏天里,窝窝头三天后就“馊”了。周四后,如果家里人没有送来后半周的窝窝头,我们就只能吃馊了的窝窝头。窝窝头上长了一层白白的茸毛,我们只能用袖口小心地将其擦去,然后吞进肚里。很无奈,但不吃就饿,所以就趁着其他同学去伙房吃饭时,我俩躲在宿舍的一角,各自悄悄地啃着“馊”了的窝窝头。这就是细节。这个细节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对人物性格的形成,乃至对人物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的影响,起到了无可替代的铺垫功能,也是我们这一代人对物质生活的渴求所致。对百红来说,就是整个集团在日益辉煌的今天还依然保持着勤俭节约美德的内在基础。
比如齐叔(百红的老父亲)给我聊起他穿上孙女给他买的新衬衫时,指着衬衫对我说这衬衫“高级”。“高级”两个字也是细节,属于个性化语言的细节。这个细节,我在《齐迹》中重复使用了一次。有一年,我从上海回槐滩看望老人家,知道他爱吃糕点,就特地从上海有名的“红宝石”买了12盒糕点。见到齐叔后,我第一时间将糕点打开,递给他。他品尝着,很自然地又说“高级”。这个“高级”与之前那个衬衫的“高级”虽然形容的不是一种物品,但文字的表现力则是一致的,而且带着人物的个性特征,使得人物更加朴实、自然、亲切、可爱。这是人物语言的细节。
再比如百红刚参加工作时,班长要每个新工人报本人穿鞋的尺码,要统一发长筒胶靴。百红当时不知道“尺码”是什么意思,从小到大就没有穿过有尺码的鞋,但又不敢问班长,就指着和自己身高相同的新工人说:“他穿多大尺码我就穿多大尺码。”结果,身高相同可脚的长度不同,发下来的鞋大了一码。大一码的鞋穿几天后的直接后果,就是百红的脚被磨出了个脓包。由于感染了,上井后不敢洗澡,只能胡乱擦擦脸,所以,脖子就黑成了“黑车轴”。去二叔家时才被二婶看见了,然后就在二叔家开始洗脖子,一遍不行两遍,两遍不行三遍,用肥皂洗,用指甲抠,用丝瓜瓤搓,洗了无数次,还是洗不干净。这描写的是人物动作的细节,而这个细节是由于不知道胶靴的“尺码”所引起的。
好的细节描写,往往可以打动读者并会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细节一定要运用有度,并不是越多越好,整篇文章都是细节,便是堆砌或者多余,非但没有妙用,反而显得累赘。
叙事散文的素材应该来源于我们熟悉的生活,人物和事件都应该使你产生过心灵震颤或者让你记忆深刻的,你可以在行文的时候有具体细节上的修饰和加工,但不能失去生活的本来面目。
叙事散文中,那些隐藏于文字后面的情与思,越厚重越真挚,就越能打动读者,越能呈现出一个文人的教养,越能显现出“文雅”和“斯文人的谈吐”。作者首先是一个对读者心存敬畏的人,一定要有丰富的人生经验作为支撑,作品也必定暗含着对生活的独特发现;同时,也一定是艺术的创造,否则,就不是“文雅的艺术”了。
对我这个年逾花甲的作者来说,所写的作品往往比年轻时的作品多了另一种东西:那就是人生的况味,人生的领悟,人生的魅力和对人生的思考。这是一种对文学的体验和感受,把这种感受写出来,呈现在纸上,就是有价值的。做有价值的事情,当然,获得的就是一种幸福。是故,我就在这充满着幸福的感觉中开始了《齐迹》一书的写作。
于我来说,写作本书的过程,犹如一个对煤海发掘的过程,需要用一盏耐得住寂寞的“心灯”,在深长、曲折的由诗文积累而形成的巷道里,去用心发掘、勘测、采掘、输送乃至提升出只属于我们煤矿工人所特有的“精神和人文的火种”,并经过一次次繁杂的淘洗、分拣,进而成为对这一精神矿藏的全新开采和深情提炼,直至将这块“琥珀”上一条又一条的“纹路”和“叶脉”呈现在读者面前。
我心中的叙述倾诉对象,首先是济煤的6000多名工友。对《齐迹》来说,他们也许是处于读者链的最末端,但我想为他们写,让他们读,让他们读得懂,从中摸到济煤的根,找到济煤的魂。让那些与百红共同历经磨难、穿过泥泞的工友们,看过《齐迹》后,了解百红的这一段往事,感悟百红的这一腔情怀,时常能回望他们一路走来的足迹,回忆他们共同拥有的难忘岁月;并能在回忆中珍惜当下,直面未来,是我创作《齐迹》最朴素的初衷。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力求感情真挚、形象丰满、情节生动、细节逼真、逻辑严密,结构完整。因为这是作品的历史价值所在,这样才能让这本书尽量存活得久一点。
以人物经历为依据的叙事散文创作,不可能像小说创作一样随心所欲,是“戴着镣铐的舞蹈”。然而,“戴着镣铐”也渴望舞出优美的舞姿。长篇叙事散文的结构,应是一种体现“秩序美”的“建筑学”,从一团乱麻到眉目清晰,要捋得清、拎得清;比如创作效果,最好是既“流泪”又“出汗”,情感抒发催人泪下,理性思辨令人出一身透汗……庆幸的是,我在拍摄人文纪录片《根在槐滩》的两年中,所到之处,都获得了齐家姊妹们朴实、敦厚、诚挚的配合和照顾,尤其是我亲爱的齐叔,给我讲述了许多惊心动魄的家族往事;还有济煤能源与百红一起打拼的工友们,给我提供了丰富生动的创作素材,没有他们每个人的生动,就没有这部书的生动。他们将永远在我眼前鲜活如初。
行文至此,天色已晚。一轮夕阳柔柔地映照在窗棂上。蓦然间,手机响了,是我的小妹从千里之外的老家济源打来的。她说:“哥,刚刚遇见你同学齐总了,哟,看着老朴素啊!穿着圆领衫、休闲裤在马路上散步。一点也不像大老板,随性、真实、自然、亲和。” 我说:“随性、真实、自然、亲和,也是我一贯追求的写作风格啊。”
(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