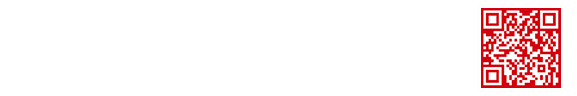暮春时节的风,带着一丝湿润,一丝季节末最后的缱绻。缱绻的春风把最后的多情给了槐林,槐林绿叶婆娑,鲜嫩纤巧的槐叶间,悄悄地吐露出一串串鼓肚的洁白月牙,一缕清甜弥漫在微风中,随着微风散向远方。
槐花开了。东坡有诗云:“槐林五月漾琼花,郁郁芬芳醉万家。春水碧波飘落处,浮香一路到天涯。”每年春末夏初,三乡十里槐花盛开。银白无瑕的槐花,馥郁芬芳,香飘百里,陶醉万家。花蕊间蜂蝶翩跹起舞,为春末夏初的大地增添了几分热闹。夏天的序幕,也就此徐徐拉开。
老家南院墙外是一大片空地,空地边挨着大路有一棵大槐树。从我记事起,大槐树就根深干粗,枝繁叶茂。四邻八舍的乡亲们,吃饭、歇晌都喜欢聚集在大槐树下。大槐树上挂了一口老钟,老钟具体什么时候挂上的,连父亲也说不清。总之,那口老钟似乎已和大槐树浑然一体。儿时的记忆中,老钟是生产队集合的口令,叮叮当当的钟声响起,乡邻们三三两两走出家门,在大槐树下集合,听队长安排当天的任务,再出发去地里干活。
大槐树下,除了是大人们的集合地,还是孩子们的乐园。单是那口老钟,就吸引着整个村东头的孩子们,每个人都想敲上几下。身手敏捷的孩子,甚至爬到槐树上,“当当当”一次敲个够,虽说免不了回家被大人狠狠地训斥,但依然乐此不疲。钟声悠荡,穿越时光,和大槐树一起成为交织在童年的温暖记忆。
槐花盛开的时节,是孩子们最高兴的时候。满树的琼花随风摇曳,串串槐花或含苞,或花瓣轻吐,清香阵阵,悠悠地随风飘散,撩拨着孩子们的味蕾。猴急的孩子早就爬上了最高的树枝,探到一串槐花,张大嘴巴,整串槐花就被直接捋到了嘴里,大口大口地咀嚼,享受着槐花最原始的清甜。爬上树的孩子不光自己吃了个过瘾,往往身兼重任。树下的一帮孩子,还巴巴地抬着头,等着树上的折了槐枝扔下来,一尝槐花的香甜。
老槐树枝叶繁茂,槐花串串缀满枝头。母亲得空时,会和邻居婶婶们一起捋槐花,做槐花蒸菜。蒸菜还得是月牙型的花苞最好,已经开了的不如没开的香甜。母亲惯常把捋好的槐花清洗干净,放在一个大竹筛子里控水。我和弟弟那时可没少在筛子里偷抓槐花吃,母亲佯装不知。控好水的槐花,要先拌上食用油,再拌适量面粉,面粉不宜太多,多了容易成坨,再放点盐和花椒粉,拌好后,水开上锅蒸,大火蒸八到十分钟即可。出锅后的槐花蒸菜,清香扑鼻,粒粒分明,晶莹剔透,每个花苞都裹着薄薄的一层面粉。盛上一碗,拌上春天刚收的新蒜汁,辛辣香甜,美味无比。抑或和鸡蛋炒着吃,别有一番清甜滋味。
最近几年,南山槐花节每年如火如荼地举行,漫山遍野的槐林,成为春末夏初人们赏花尝鲜的新去处。为避开人流高峰,我和几个朋友,一般会选择下午去。下午3点左右出发,带上摘槐花的工具,带上好心情,一起出发前往南山。其实也不全是为了摘槐花,出行是需要理由的,就像有些时候、有些事情,我们需要一个理由去说服自己,需要一个理由去找到心理平衡的支撑点,如此而已。于是,摘槐花就成了最好的出行理由。
槐树繁殖力极强。俗话说:“一年一棵,两年一窝,三年一坡。”南山的槐林,一年更比一年繁茂,盛开时节,峰峰岭岭,琼花满山,游人如织。因为南山槐林茂盛,山路十八弯,几乎从每个路口拐进去,都能看到满坡的槐花。微风吹过,清香浮动,沁人心脾。到南山摘槐花,朋友每年都会选择不同的路口进山。按照朋友的说法,大路边的早就被人们摘完了,剩下那些高枝上的槐花又够不着。
去年去得晚了,槐花多数已凋落,只在树梢尚有部分晚开的花,洁白的花串独立梢头,摇曳着动人的风姿。几个人分工合作,有人勾枝,有人负责摘花。搁以前,开花的肯定看不上,只要未开的花苞,去晚了就顾不上那么多了,只要是发白的花串,全都收入囊中。斜阳西下,天色虽晚,但囊中收获颇丰,一行人欣欣然踏着暮色,携花香而归。
收获的槐花,除了做槐花蒸菜,还可以摊槐花饼、包饺子、包包子。因为摘的槐花颇多,就商量着几家合伙包包子。于是,抽了半天时间,淘洗槐花、和面、盘馅,各负其责,一场轰轰烈烈的“包包子运动”开始了。从早上一直忙活到中午,蒸了好几笼包子。吃饭时间更是热闹,几家的孩子和大人挤了满满一屋子。氤氲着槐花清香的屋子,嬉闹欢乐的人间烟火,最是抚慰人心。世事喧嚣又如何,温婉岁月中的一缕烟火,才是心灵安然的一隅归宿。
“蝉发一声时,槐花带两枝。”伴着槐花的香甜,春光逐渐走远,夏的脚步悄悄临近。这一场槐花盛宴,风起芬芳,浮香十里,终像一场梦,馨香在光阴的长廊中,随着时光的轮回,渐渐弥散在如水的岁月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