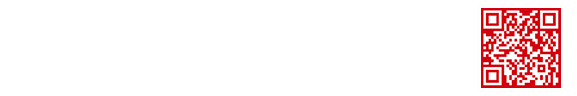做人有做人的格局,植物也有植物的格局。只不过,植物的格局,仿佛并不在于植物与植物之间。它们的范围,比人与人之间的格局大得多,也广得多。
一株玉米,无论是长在山丘还是长在院落,都如同植物界的绅士,默默无闻,勤勤恳恳,在自己的那一小块地方,认真地生长。它的生长范围很小,地面下的世界,只有几个巴掌大的地方。它和杂草与周围的树木共同生长,共同沐浴阳光,从不计较谁的土地占有得多,谁占有得少。幼苗生长出来的时候,它的心就凝结着一滴露。它从出生顶破土壤开始,一露头,看到这个世界,就流下了欢喜的泪滴。它不明白生命的赋予,对于它只是一个偶然,完全没有太多的精心策划,可它却欢喜地努力地去长高,而这样的长高,也只是生命的本然。
为此,它专注于拔高自己的身体,专注于早点变得周身青绿,专注于抽穗扬花早早结出饱满的果实。一声“脆响”,玉米落入了一个竹筐里,依然保持着绅士的风度,仿佛这样的奉献就应当如此。一阵秋风刮过头顶,吹着枯黄的衣裳,它在瑟瑟秋风里,沉默不语。直至一把镰刀收割了它,把它送入灶火里。它欢快地唱着歌,用火焰的舞蹈来颂唱生命的赞歌。
玉米的格局仿佛很小,玉米的格局又仿佛很大。一只蝴蝶,在它的头顶飞来飞去,最后选择离开,落在前方的一朵花上。那朵花只不过是格桑花或者野豌豆花,但是,它却不愿意在青色的绅士面前停留,落在它的衣襟,哪怕只停留一会儿,给它戴上一枚别致的胸针,都不会。对此,玉米只绅士地保持站立的姿态,不会趁着风云变幻窃窃私语。
它不争天地,不争肥水,不争沃壤。它只与清风明月为伴。
玉米的格局的确太小了,不借助清泉沃壤。它的生长范围,也就只能是脚下。一块巴掌大的地方,抬头也只能看到巴掌大的地方。这样的视野范围,怎么能算得上开阔呢?这样的认知,又怎么能称得上格局呢?见过长在牛粪旁的玉米,也见过长在老槐树下的玉米,更见过长在水洼旁的玉米。它们长得都不一样。长在牛粪旁的玉米,玉米秆又粗又壮;长在老槐树下的玉米,株秆挺拔直立;长在洼地的玉米,植株瘦弱不堪。可是,它们又仿佛都一样,永远那么绅士地站立着。清风摇曳着它们细长的叶子,月光拂照着它们挺立的身姿。它们彼此之间,从没有因为你在水洼处,我在槐树旁,就觉得彼此之间有什么不同,也从未因为你的植株过于瘦弱,我的植株格外粗壮而感到自惭形秽或骄傲自满。
如果真要说,它们都共同引以为荣的,就是人类赐予了它们一个儒雅又美好的名字——“玉米”。为此,它们还真是“沾沾自喜”。想一想,哪儿有一种米以“玉”相称呢?虽然人们赋予了玉米“金玉满堂、岁岁平安、招财进宝”等多种寓意,但是玉米只觉得“温润如玉,灵魂芬芳”的玉米,才是一棒好玉米。为此,它们深信这是自己的使命。
玉米不懂“夏虫不可语冰,井蛙不可语海”的真正内涵,更不懂“登高山知山之巍峨,临大海知海之浩瀚”的道理。它们只管关注自己的脚下,只管专注于自己的内心。一株玉米,太过渺小了;可一片玉米,却可以形成一片青纱帐;温饱时,一棒玉米算不上美食;饥饿时,一棒玉米比得上所有珍宝。
不要再瞧不起一株玉米。它们生命的格局,比我们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