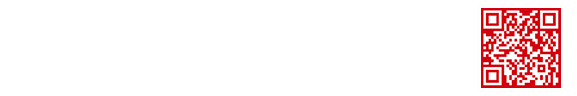巧了,那天下午,我刚到办公室,手机铃声就响了,是快递小哥打来的,说有我的包裹,让签收一下。我思来想去,最近也没有网购什么东西啊,哪儿来的包裹?再三核实确认无误后,怀着疑惑和好奇,我急忙到一楼门岗,签收,拆封,哦,原来是一本书——明亮新出版的散文集。
真好。30万字的集子沉甸厚实,素雅精美,不枉费他多年的心血。纳闷的是,同居一座小城,一东一西不过10公里的距离,还用快递?电话打过去,他立刻挂了,微信倒很快来了:“疫情防控,多有不便,委托小哥呈上。各自安好。”后面跟着一连串狡黠的“笑脸”。
明亮原本是写诗的,自称“90”后里的小老大,2011年从师范毕业后,去了山区的一所中学教语文。多年前,我们参加了一个笔会,回来后以文相交。那是一个生态文明主题的小型林业笔会。自由活动的时候,他一会儿帮这个拿水杯,一会儿替那个分发资料。金秋的山里很凉爽,他跑前跑后,把自己弄得一脸的汗水,勤快,心细,也知趣,风风火火里透着谦卑。说来也怪,明明20岁出头,他却长得比较“着急”。脑门宽宽的,头发没有这个年龄该有的茂盛,白胖胖的娃娃脸,敦实的身板,憨憨厚厚的。就是这么一个外表粗犷的人,能写得一手好诗,细腻,缜密,唯美,作品很难和作者对上号。晚上在林场欢聚,他似乎有点醉,忘乎所以地高歌狂舞,自我陶醉成众人的一道开胃的菜,也为笔会添了不少乐趣。或许都是从事文字工作的缘故,我们渐渐熟识起来。虽然我大他10多岁,闲来小聚,我也会叫上他。每每聚会未完,他就得提前离开,赶回山里的校舍,不然就耽误翌日的课程。他十分不情愿,明显的兴致未尽。那时,他最羡慕高楼里的万家灯火,但现实的骨感,让他只能在诗歌里渴盼有一盏灯能真正属于他。
教学之余,明亮笔耕不辍,我经常在媒体上看到他的作品。我曾问过他:“整天和一群学生娃娃厮混已经够费心了,还有闲情写诗?”他说:“总得有点爱好吧,不能百无聊赖啊。”也是,远离闹市,那时的条件,不如现在这么便捷。闲暇,总得让心有所寄有所依。诗以言志,或许明亮写诗是排遣心绪吧。“把爱好做到极致,其实也是想给孩子们做个榜样。”他说,钻一行,坚持3年能成行家,5年能成专家,坚持一辈子,就能成为大国工匠。如此见地,他就有了明确的方向和目标。他的勤奋,他的执着,让他有了不俗的业绩,也给他创造了改变命运的机遇。没过两年,他就被调往市里的一所中学编排校报。全市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后,整治“空心村”,迁户并村,生源分流,他原来所在的学校也并入平原乡镇的一所学校。
憨人自有憨福。外表憨厚的明亮先是和同校的一个数学老师成了家,后来赶上教育系统的集资建房,筹集、借贷,总算满足了他在诗歌里反复吟唱挂牵的那份热望。环境的改变,境遇的多变,让他在诗歌里感慨感怀又感恩。女儿出生后,琐碎的生活节奏更加紧凑,但这并没有磨灭他心中的那份憧憬。他依然有作品发表,不断在朋友圈晒幸福。不同于以往,他的诗歌里少了清风蝉鸣,少了弯月浮香,少了山水草木的四季物语,多了些人间的烟火气息和脚踏大地的充实丰盈,而且开始写起了散文和教育随笔。
其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各自忙碌,断了联系。我也鲜见他的作品,微信朋友圈也不再那么热闹,似乎有事不便打扰。年底聚会,他才告知大半年来他在复旦大学读硕士,脱产学习,很大程度上为着职称晋升的考虑,而且给每人送了一本诗集。言语之间,沉稳,内敛,也更加成熟。
读完硕士的明亮回来后,重回教学岗位,一头学校一头家。和多数人一样,他也难逃被纷纷扰扰羁身绊心的桎梏。难得的是,他身在俗世翻滚,心在荒村听雨,依然坚守着自己的爱好,更加细致地捕捉时代的个人印记和生活的不同质感,并赋予其独特的个体体验,且歌且行,且行且获,那些付出的辛劳和喜悦,那些心湖泛起的涟漪和浪花,都融入了记录生活变迁和心路历程的文字里。
只是,一边筹备书稿,一边还要照顾怀了二宝的爱人,也真够他忙的。
今夏,天气反复无常,一如这让人猝不及防的疫情。耗时两个星期,我断断续续看完了这本集子,准备写篇评论以文答谢。闲来无事,正想着怎么下笔,明亮发来微信:“瓜熟蒂落,挺‘好’,疫情松了,一起闹闹。”
我立刻明白,明亮添了弄璋之喜。喜人之喜,乐人之乐,是为大喜大乐。当年的毛头小伙,如今已入而立之年,双双丰收。欣喜之余,我给他发去了一个大大的红包,并恭贺他又得偿所愿。
须臾之间,他回复:“谢谢,还有嘞。”后面跟着一连串的“笑脸”,还是那么狡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