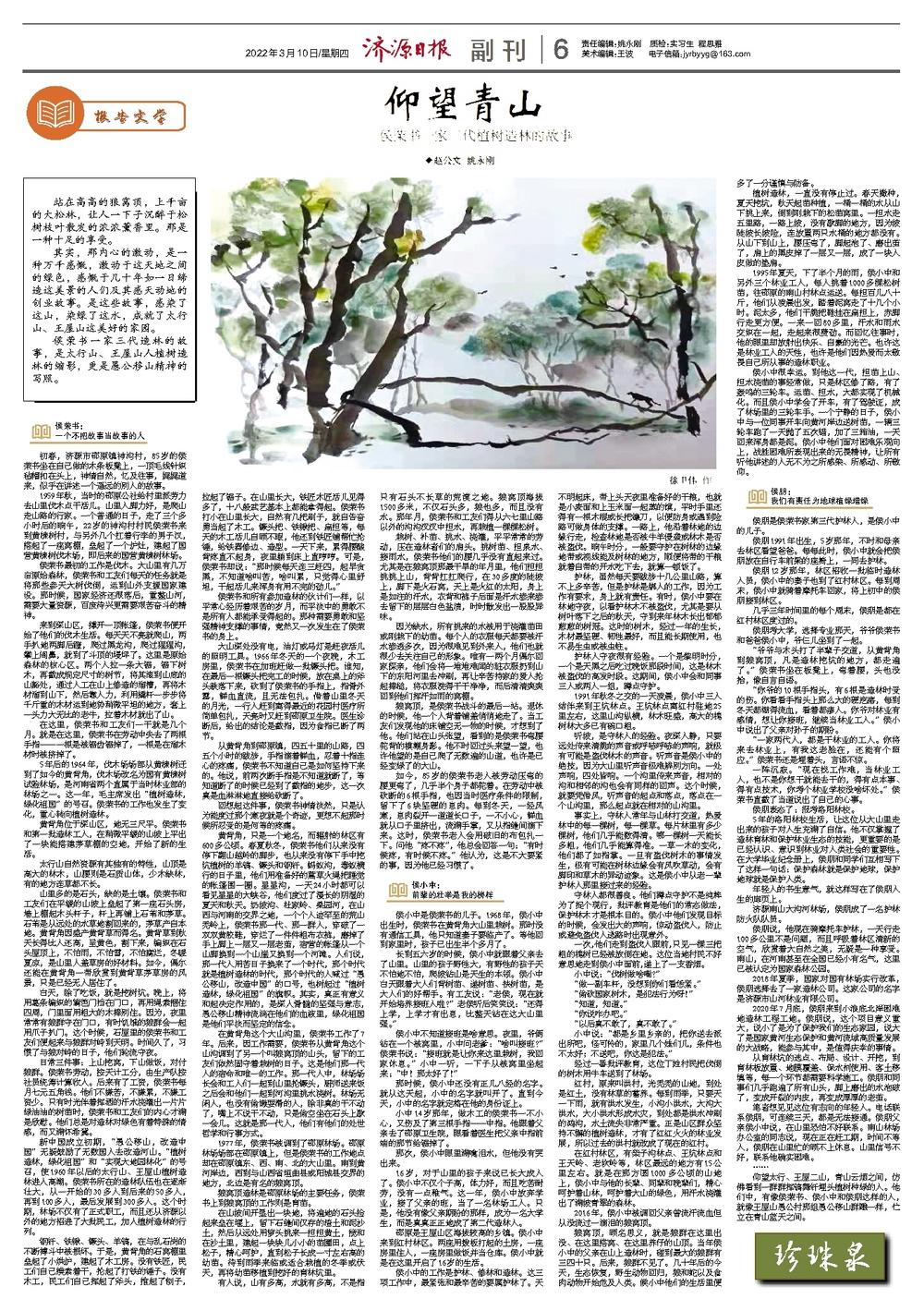站在高高的狼窝顶,上千亩的大松林,让人一下子沉醉于松树枝叶散发的浓浓薰香里。那是一种十足的享受。
其实,那内心的激动,是一种万千感慨,激动于这天地之间的绿色,感慨于几十年如一日缔造这美景的人们及其感天动地的创业故事。是这些故事,感染了这山,染绿了这水,成就了太行山、王屋山这美好的家园。
侯荣书一家三代造林的故事,是太行山、王屋山人植树造林的缩影,更是愚公移山精神的写照。
侯荣书:
一个不把故事当故事的人
初春,济源市邵原镇神沟村,85岁的侯荣书坐在自己做的木条板凳上,一顶毛线针织毡帽扣在头上,神情自然,忆及往事,娓娓道来,似乎在讲述一个遥远的别人的故事。
1959年秋,当时的邵原公社给村里派劳力去山里伐木点干活儿。山里人脚力好,是爬山走山路的行家。一个普通的日子,走了三个多小时后的晌午,22岁的神沟村村民侯荣书来到黄楝树村,与另外几个扛着行李的男子汉,搭起了一座窝棚,垒起了一个炉灶,建起了国营黄楝树伐木场,即后来的国营黄楝树林场。
侯荣书最初的工作是伐木。大山里有几万亩原始森林,侯荣书和工友们每天的任务就是将那些参天大树伐倒,运到山外支援国家建设。那时候,国家经济还很落后,重整山河,需要大量资源,百废待兴更需要艰苦奋斗的精神。
来到深山区,撑开一顶帐篷,侯荣书便开始了他们的伐木生活。每天天不亮就爬山,两手扒地两脚后蹬,爬过黑龙沟,爬过猩猩沟,攀上阎鼻,就到了斗顶的墁坪了。这里是原始森林的核心区。两个人拉一条大锯,锯下树木,再截成规定尺寸的树节,将其滚到山底的山豁处,通过人工在山上修造的溜槽,再将木材溜到山下,然后靠人力,利用撬杆一步步将千斤重的木材运到地势稍微平坦的地方,套上一头力大无比的老牛,拉着木材就出了山。
在这里,侯荣书和工友们一干就是几个月。就是在这里,侯荣书在劳动中失去了两根手指——一根是被锯齿锯掉了,一根是在溜木材时被挤掉了。
5年后的1964年,伐木场场部从黄楝树迁到了如今的黄背角,伐木场改名为国有黄楝树试验林场,是河南省两个直属于当时林业部的林场之一。这一年,毛主席发出“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号召。侯荣书的工作也发生了变化,重心转向植树造林。
黄背角位于深山区,地无三尺平。侯荣书和第一批造林工人,在稍微平缓的山坡上平出了一块能搭建茅草棚的空地,开始了新的生活。
太行山自然资源有其独有的特性,山顶是高大的林木,山腰则是石质山体,少木缺林,有的地方连草都不长。
山里多的是石头,缺的是土壤。侯荣书和工友们在平缓的山坡上垒起了第一座石头房,墙上棚起木头杆子,杆上再铺上石苇和茅草。石苇是从远处的水草地割回来的,茅草产自本地。黄背角因盛产黄背草而得名。黄背草到秋天长得比人还高,呈黄色,割下来,编织在石头屋顶上,不怕雨,不怕雪,不怕腐烂,冬暖夏凉,是山里人盖草房的好材料。如今,偶尔还能在黄背角一带欣赏到黄背草茅草房的风景,只是已经无人居住了。
白天,除了吃饭,就是挖树坑。晚上,将用葛条编织的篱笆门挡在门口,再用绳索捆住四周,门里面用粗大的木棒别住。因为,夜里常常有狼群守在门口,有时饥饿的狼群会一起用爪子扒门。这个时候,石屋里的侯荣书和工友们便起来与狼群对峙到天明。时间久了,习惯了与狼对峙的日子,他们轮流守夜。
日常三件事:上山挖窝,下山做饭,对付狼群。侯荣书劳动,按天计工分,由生产队按社员统筹计算收入。后来有了工资,侯荣书每月七元五角钱。他们不嫌苦,不嫌累,不嫌工资少。只有时光伴着挥洒的汗水浇灌出一片片绿油油的树苗时,侯荣书和工友们的内心才满是欣慰。他们总是对造林对绿色有着特殊的情感,而又满怀希冀。
新中国成立初期,“愚公移山,改造中国”无疑鼓励了无数国人去改造河山。“植树造林,绿化祖国”和“实现大地园林化”的号召,使1960年以后的太行山、王屋山植树造林进入高潮。侯荣书所在的造林队伍也在逐渐壮大,从一开始的30多人到后来的50多人,再到100多人,最后发展到300多人。这个时期,林场不仅有了正式职工,而且还从济源以外的地方招进了大批民工,加入植树造林的行列。
钢钎、铁锹、镢头、羊镐,在与乱石岗的不断搏斗中被损坏。于是,黄背角的石窝棚里垒起了小烘炉,建起了木工房。没有铁匠,民工们自己摸索着干,抡起了打铁的锤子。没有木工,民工们自己挥起了斧头,推起了刨子,拉起了锯子。在山里长大,铁匠木匠活儿见得多了,十八般武艺基本上都能拿得起。侯荣书打小在山里长大,自然有几把刷子,就自告奋勇当起了木工。镢头把、铁锹把、扁担等,每天的木工活儿自顾不暇,他还到铁匠铺帮忙抡锤,给铁器修边、造型。一天下来,累得腰酸背疼直不起身,夜里躺到床上直哼哼。可是,侯荣书却说:“那时候每天连三赶四,起早贪黑,不知道啥叫苦,啥叫累,只觉得心里舒坦,干起活儿来浑身有用不完的劲儿。”
侯荣书和所有参加造林的伙计们一样,以平常心经历着艰苦的岁月,而平淡中的勇敢不是所有人都能承受得起的。那种需要勇敢和坚强精神支撑的事情,竟然又一次发生在了侯荣书的身上。
大山深处没有电,油灯或马灯是赶夜活儿的照明工具。1966年冬天的一个夜晚,木工房里,侯荣书在加班赶做一批镢头把。谁知,在最后一根镢头把完工的时候,放在桌上的斧头跌落下来,砍到了侯荣书的手指上,指骨外露,鲜血直流,且无法包扎。借着山里冬天的月光,一行人赶到离得最近的花园村医疗所简单包扎,天亮时又赶到邵原卫生院。医生诊断后,给出的结论是截指,因为食指已断了两节。
从黄背角到邵原镇,四五十里的山路,四五个小时的跋涉,手指滴着鲜血,忍着十指连心的疼痛,侯荣书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坚持下来的。他说,前两次断手指是不知道就断了,等知道断了的时候已经到了截指的地步,这一次真是血淋淋地直接给砍断了。
回想起这件事,侯荣书神情淡然,只是认为能度过那个寒夜就是个奇迹,更想不起那时候所忍受的是何等的疼痛。
黄背角,只是一个地名,而辐射的林区有600多公顷。春夏秋冬,侯荣书他们从来没有停下翻山越岭的脚步,也从来没有停下手中挖坑植树的羊镐、镢头和钢钎。蚂蚁沟,毒蚁横行的日子里,他们用准备好的蒿草火绳把睡觉的帐篷围一圈。星星沟,一天24小时都可以看见星星的大峡谷,他们度过了漫长的阴湿的夏天和秋天。奶坡沟、杜家岭、桑园河,在山西与河南的交界之地,一个个人迹罕至的荒山秃岭上,侯荣书那一代、那一群人,穿破了一双双黄胶鞋,穿烂了一件件粗布衣裤,磨掉了手上脚上一层又一层老茧,宿营的帐篷从一个山脚换到一个山崖又换到一个河滩。人们说,那一代人用苦日子换来了一个时代,那个时代就是植树造林的时代,那个时代的人喊过“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口号,也树起过“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旗帜。其实,真正有意义和起决定作用的,是深入骨髓的坚强与意志,愚公移山精神流淌在他们的血液里,绿化祖国是他们平淡而坚定的信念。
在黄背角这个大山沟里,侯荣书工作了7年。后来,因工作需要,侯荣书从黄背角这个山沟调到了另一个叫狼窝顶的山头,留下的工友们依然固守着栽树的日子。这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宿命和唯一的工作。那一代人中,林场场长会和工人们一起到山里抡镢头,厨师送来饭之后会和他们一起到河沟里挑水浇树。林场无闲人,也没有偷懒耍滑的人,除非真的干不动了,嘴上不说干不动,只是偷空坐在石头上歇一会儿。这就是那一代人,他们有他们的处世哲学和行事方式。
1977年,侯荣书被调到了邵原林场。邵原林场场部在邵原镇上,但是侯荣书的工作地点却在邵原镇东、西、南、北的大山里。南到黄河岸边,西到与山西省垣曲县或阳城县交界的地方,北边是有名的狼窝顶。
狼窝顶造林是邵原林场的主要任务,侯荣书上到狼窝顶的工作则是育苗。
在山坡间开垦出一块地,将遍地的石头捡起来垒在堰上,留下石缝间仅存的渣土和泥沙土,然后从远处用箩头挑来一担担黄土,搅和在沙土里,建起一块块儿小小的苗圃田,点上松子,精心呵护,直到松子长成一寸左右高的幼苗。待到雨季来临或适合栽植的冬季或伏天,再将幼苗移植到挖好的育林坑里。
有人说,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不是指只有石头不长草的荒漠之地。狼窝顶海拔1500多米,不仅石头多,狼也多,而且没有水。那年月,侯荣书和工友们得从六七里山路以外的沟沟汊汊中担水,再栽植一棵棵松树。
栽树、补苗、挑水、浇灌,平平常常的劳动,压在造林者们的肩头。挑树苗、担泉水、接雨水,侯荣书他们的腰几乎没有直起来过。尤其是在狼窝顶那最干旱的年月里,他们担担挑挑上山,背背扛扛爬行,在30多度的陡坡上,脚下是火石窝,天上是火红的太阳,身上是如注的汗水,衣背和裤子后面是汗水渗来渗去留下的层层白色盐渍,时时散发出一股股异味。
因为缺水,所有挑来的水被用于浇灌苗田或刚栽下的幼苗。每个人的衣服每天都要被汗水渗透多次,因为很难见到外来人,他们也就很少去关注自己的形象。唯有一两个月偶尔回家探亲,他们会将一堆堆难闻的脏衣服扔到山下的东阳河里去冲刷,再让辛苦持家的爱人抡起棒槌,将衣服洗得干干净净,而后清清爽爽回到他们挥汗如雨的窝棚。
狼窝顶,是侯荣书战斗的最后一站。退休的时候,他一个人背着铺盖悄悄地走了。当工友们发现他的床铺空无一物的时候,才想到了他。他们站在山头张望,看到的是侯荣书弯腰驼背的模糊身影。他不时回过头来望一望,也许他望的是自己爬了无数遍的山道,也许是已经变绿了的大山。
如今,85岁的侯荣书老人被劳动压弯的腰更弯了,几乎半个身子都驼着。在劳动中被砍断的6根手指,也因当时医疗条件的限制,留下了6块坚硬的息肉。每到冬天,一经风寒,息肉裂开一道道长口子,一不小心,鲜血就从口子里挤出,流满手掌,又从指缝间滴下来。这时,侯荣书老人会用破旧的布包扎一下。问他“疼不疼”,他总会回答一句:“有时候疼,有时候不疼。”他认为,这是不大要紧的事,因为他已经习惯了。
侯小中:
前辈的壮举是我的榜样
侯小中是侯荣书的儿子。1968年,侯小中出生时,侯荣书在黄背角大山里栽树。那时没有通信工具,他只知道妻子要临产了。等他回到家里时,孩子已出生半个多月了。
长到五六岁的时候,侯小中就跟着父亲去了山里。山里的孩子野性大,有野性的孩子天不怕地不怕,爬坡钻山是天生的本领。侯小中白天跟着大人们背树苗、递树苗、扶树苗,是大人们的好帮手。有工友说:“老侯,现在就开始培养接班人啦?”老侯听后笑笑说:“还得上学,上学才有出息,比整天钻在这大山里强。”
侯小中不知道接班是啥意思。夜里,爷俩钻在一个被窝里,小中问老爹:“啥叫接班?”侯荣书说:“接班就是让你来这里栽树,我回家休息。”小中一听,一下子从被窝里坐起来:“中!那太好了!”
那时候,侯小中还没有正儿八经的名字。就从这天起,小中的名字就叫开了。直到今天,小中的名字就定格在他的身份证上。
小中14岁那年,做木工的侯荣书一不小心,又伤及了第三根手指——中指。他跟着父亲去了邵原卫生院,眼看着医生把父亲中指前端的那节给锯掉了。
那次,侯小中眼里满噙泪水,但他没有哭出来。
16岁,对于山里的孩子来说已长大成人了。侯小中不仅个子高,体力好,而且吃苦耐劳,没有一点稚气。这一年,侯小中放弃学业,接了父亲的班,当了一名林场工人。只是,他没有像父亲期盼的那样,成为一名大学生,而是真真正正地成了第二代造林人。
邵原是王屋山区海拔较高的乡镇。侯小中来到红村林区。两座用拨板打起的土房,一座房里住人,一座房里做饭并当仓库。侯小中就是在这里开启了16岁的生活。
侯小中的工作是护林、修林和造林。这三项工作中,最紧张和最辛苦的要属护林了。天不明起床,带上头天夜里准备好的干粮,也就是小麦面和上玉米面一起蒸的馍,平时手里还得有一根木棍或长把镰刀,以便防身或遇到险路可做身体的支撑。一路上,他沿着林地的边缘行走,检查林地是否被牛羊侵袭或林木是否被盗伐。晌午时分,一般要守护在树林的边缘地带或视线能及树林的地方,顺便将带的干粮就着自带的开水吃下去,就算一顿饭了。
护林,虽然每天要跋涉十几公里山路,算不上多辛苦,但是护林是绑人的工作,因为工作有要求,身上就有责任。有时,侯小中要在林地守夜,以看护林木不被盗伐,尤其是要从树叶落下之后的秋天,守到来年林木长出郁郁葱葱的树冠。这时的树木,经过一年的生长,木材最坚硬、韧性最好,而且能长期使用,也不易生虫或被虫蛀。
护林人守夜很有经验。一个是黎明时分,一个是天黑之后吃过晚饭那段时间,这是林木被盗伐的高发时段。这期间,侯小中会和同事三人或两人一组,蹲点守护。
1991年秋冬之交的一天凌晨,侯小中三人结伴来到王坑林点。王坑林点离红村驻地25里左右,这里山沟纵横,林木旺盛,高大的槐树林大多已有碗口粗。
听坡,是守林人的经验。夜深人静,只要远处传来清脆的声音或呼哧呼哧的声响,就极有可能是盗伐林木的声音。听声音是侯小中的绝技,因为大山里听声音极难辨别方向。一处声响,四处皆响。一个沟里传来声音,相对的沟和相邻的沟也会有同样的回声。这个时候,就要凭借风,听声音的起点和落点,落点在一个山沟里,那么起点就在相对的山沟里。
事实上,守林人常年与山林打交道,热爱林中的每一棵树,每一棵草。每片林里有多少棵树,他们几乎能数得清。哪一棵树一天能长多粗,他们几乎能算得准。一草一木的变化,他们都了如指掌。一旦有盗伐树木的事情发生,极有可能在树林边缘会有风吹草动,会有脚印和草木的异动迹象。这是侯小中从老一辈护林人那里接过来的经验。
守林人都很善良。他们蹲点守护不是纯粹为了捉个现行,批评教育是他们的常态做法,保护林木才是根本目的。侯小中他们发现目标的时候,会发出大的声响,惊动盗伐人,防止或避免盗伐人逃路时出现意外。
一次,他们走到盗伐人跟前,只见一棵三把粗的槐树已经被放倒在地。这位当地村民不好意思地走到侯小中面前,递上了一支香烟。
小中说:“伐树做啥嘞?”
“做一副车杆,没想到你们看恁紧。”
“偷砍国家树木,是犯法行为呀!”
“知道,知道。”
“你说咋办吧。”
“以后真不敢了,真不敢了。”
小中说:“都是乡里乡亲的,把你送去派出所吧,怪可怜的,家里几个娃们儿,条件也不太好;不送吧,你这是犯法。”
经过一番批评教育,这位丁姓村民把伐倒的树木用牛车送到了林场。
红村,原来叫洪村,光秃秃的山地,到处是红土,没有林草的蓄养。每到雨季,只要天一下雨,就有洪水发生,小沟小洪水,大沟大洪水,大小洪水形成水灾,到处都是洪水冲刷的鸿沟,水土流失非常严重。正是山区群众坚持不懈的植树造林,才有了红红火火的林业发展,所以过去的洪村就改成了现在的红村。
在红村林区,有柴子沟林点、王坑林点和王天岭、老坎岭等,林区最远的地方有15公里左右。就是在那方圆1000多公顷的山地上,侯小中与他的长辈、同辈和晚辈们,精心呵护着山林,呵护着大山的绿色,用汗水浇灌出了满坡青翠的森林。
2016年,侯小中被调回父亲曾流汗流血但从没流过一滴泪的狼窝顶。
狼窝顶,顾名思义,就是狼群在这里出没、在这里搭窝、在这里养仔的山顶。当年侯小中的父亲在山上造林时,碰到最大的狼群有三四十只。后来,狼群不见了。几十年后的今天,生态恢复,野生动物回归,狼和蛇以及食肉动物开始危及人类。候小中他们的生活里便多了一分谨慎与防备。
植树造林,一直没有停止过。春天撒种,夏天挖坑,秋天起苗种植,一桶一桶的水从山下挑上来,倒到刚栽下的松苗窝里。一担水走五里路,一路上坡,没有歇脚的地方,因为坡陡坡长坡险,连放置两只水桶的地方都没有。从山下到山上,腰压弯了,脚起泡了、磨出茧了,肩上的黑皮掉了一层又一层,成了一块人皮做的垫肩。
1995年夏天,下了半个月的雨,侯小中和另外三个林业工人,每人挑着1000多棵松树苗,往邵原的南山村林点运送。每担百儿八十斤,他们从凌晨出发,踏着泥窝走了十几个小时。泥太多,他们干脆把鞋挂在扁担上,赤脚行走更方便。一来一回80多里,汗水和雨水交织在一起,走起来很费劲。而回忆往事时,他的眼里却放射出快乐、自豪的光芒。也许这是林业工人的天性,也许是他们因热爱而太敬畏自己所从事的造林职业。
侯小中很幸运。到他这一代,担苗上山、担水浇苗的事经常做,只是林区修了路,有了轰鸣的三轮车。运苗、担水,大都实现了机械化。而且侯小中学会了开车,有了驾驶证,成了林场里的三轮车手。一个宁静的日子,侯小中与一位同事开车向黄河岸边送树苗,一辆三轮车跑了一天抛了五次锚,加了三箱油,一天回来浑身都是泥。侯小中他们面对困难乐观向上,战胜困难所表现出来的无畏精神,让所有听他讲述的人无不为之所感染、所感动、所敬仰。
侯朋:
我们有责任为地球植绿增绿
侯朋是侯荣书家第三代护林人,是侯小中的儿子。
侯朋1991年出生,5岁那年,不时和母亲去林区看望爸爸。每每此时,侯小中就会把侯朋放在自行车前梁的座椅上,一同去护林。
侯朋12岁那年,林区招收一批临时造林人员,侯小中的妻子也到了红村林区。每到周末,侯小中就骑着摩托车回家,将上初中的侯朋接到林区。
几乎三年时间里的每个周末,侯朋是都在红村林区度过的。
侯朋考大学,选择专业那天,爷爷侯荣书和爸爸侯小中,爷仨儿坐到了一起。
“爷爷与木头打了半辈子交道,从黄背角到狼窝顶,凡是造林挖坑的地方,都走遍了。”侯荣书坐在板凳上,弯着腰,头也没抬,像自言自语。
“你爷的10根手指头,有6根是造林时受的伤。你看看手指头上那么大的硬疙瘩,每到冬天都绷得流血,看着都瘆人。你爷对林业有感情,想让你接班,继续当林业工人。”侯小中说出了父亲对孙子的期盼。
“一家两代人,都是干林业的工人。你将来去林业上,有我这老脸在,还能有个照应。”侯荣书还是埋着头,言语不惊。
一阵沉寂。“现在找工作难,当林业工人,也不是你想干就能去干的,得有点本事、得有点技术,你考个林业学校没啥坏处。”侯荣书直截了当道说出了自己的心事。
侯朋表态了:报考洛阳林校。
5年的洛阳林校生活,让这位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孩子对人生充满了自信。他不仅掌握了造林育林和保护林业生态的技能,更重要的是已经认识、意识到林业对人类社会的重要性。在大学毕业纪念册上,侯朋和同学们互相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保护森林就是保护地球,保护地球就是保护人类。
年轻人的书生意气,就这样写在了侯朋人生的扉页上。
济源南山大沟河林场,侯朋成了一名护林防火队队员。
侯朋说,他现在骑摩托车护林,一天行走100多公里不是问题,而且呼吸着林区清新的空气,欣赏着大自然之美,无疑是一种享受。南山,在河南甚至在全国已经小有名气,这里已被认定为国家森林公园。
2018年夏季,国家对国有林场实行改革,侯朋选择去了一家造林公司。这家公司的名字是济源市山河林业有限公司。
2020年7月底,侯朋来到小浪底北岸困难地造林工程工地。侯朋说,这个项目意义重大,说小了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生态家园,说大了是国家黄河生态保护和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大战略,能参与其中,是值得庆幸的事情。
从育林坑的选点、布局、设计、开挖,到育林板放置、地膜覆盖、保水剂使用、客土移填等,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科学施工。侯朋和同事们几乎跑遍了所有山头,脚上磨出的水泡破了,变成开裂的内皮,再变成厚厚的老茧。
笔者想见见这位有志向的年轻人。电话联系侯朋,可连续三天,都是无法接通。侯朋父亲侯小中说,在山里恐怕不好联系。南山林场办公室的同志说,现在正在赶工期,时间不等人,侯朋在山里忙的顾不上休息。山里信号不好,联系他确实困难。
……
仰望太行、王屋二山,青山云烟之间,仿佛看到一群群挥镐舞钎埋头植树种绿的人。他们中,有像侯荣书、侯小中和侯朋这样的人,就像王屋山愚公村那组愚公移山群雕一样,伫立在青山蓝天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