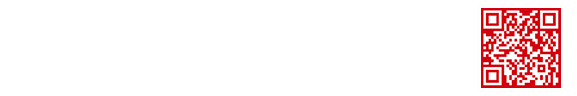肖培根,我国药用植物和中药资源研究的主要奠基人和学术带头人,国际著名的药用植物与传统药物学家,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他于1932年出生于上海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1949年考入厦门大学生物系;1953年春提前毕业,被分配到中央卫生研究院药物学系(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前身)。他历任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首任所长、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咨询团顾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临时顾问等职。
他26岁挑起全国第一次中药普查的大梁,第一次摸清了“家底”;他作为新中国最早的“传统医药大使”,从西非四国开始走向世界各地,将中医药文化带到五洲四海;他为打破西方的封锁,在国产资源替代进口的探索中,创立了崭新的学科——药用植物亲缘学。
摸清全国中药资源的“家底”
1932年2月2日,肖培根出生于上海市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是家中长子。父亲肖贺昌早年留学德国,回国后曾任大学教授、政府高级职员。母亲张英志曾就读于浙江大学,当过小学教师和会计。肖培根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正值日寇侵华。父亲因不肯为伪政权做事而失业,家里沦落到三餐难以为继的地步。但是,无论生活多么拮据,父母没有让一个孩子辍学,兄妹五人皆大学毕业。
1953年春,肖培根提前半年修满学分,以优秀成绩毕业。奉卫生部调令,他从厦门赶到北京。当年从厦门坐火车、乘汽车,半个月才到北京,舟车劳顿,他的体重竟减了5公斤。“当时国家统一分配,中央卫生研究院跟国家提出要一个懂植物生理专业的人,所以我就来了。我们大学只有两个人被分到了北京。”肖培根说。
虽然当时全国人才匮乏,但中央卫生研究院汇集了许多国内一流专家,包括赵橘黄、姜达衢、傅丰永、叶三多、周梦白等。那时,药物学系只有肖培根一个刚刚分配来的大学生。谦逊好学、阳光俊朗的肖培根,得到了专家们的真诚传授,也获得了独挑大梁的机会。临床必备的麦角制剂,是用于治疗产后子宫出血、产后子宫复旧不全等症的进口药。由于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行封锁,药品紧缺,寻找药源的任务就落在了年仅21岁的肖培根身上。他毕业那年就奔赴河北省张北、沽源县,寻觅野生麦角资源。野外调查异常艰苦,他经常雇一辆马车拉着铺盖行李,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艰辛换来丰硕的回报。他在荒野中找到了寄生在拂子茅上的野生麦角,含量非常高。“野生麦角有效成分的含量是其他种类不能比拟的”,为国产麦角新碱的研发铺平了道路,中国有了物美价廉的救命药。1954年,《药学通报》上发表了肖培根学术生涯的第一篇论文——《河北沽源县药用植物的调查》。
1958年,卫生部下达了全国第一次中药普查任务,交由药物研究所药用植物研究室负责。作为室主任,这个重担落在了26岁的肖培根肩上。尽管他的团队有38人,但都是比他更年轻的大学生,行吗?
全国第一次中药普查意义重大。国人吃了上千年的中药,但“家底”无人知晓。作为国家战略资源说不清楚当然不行,但是要完成任务绝非易事。“那时候,可以用4个字来形容,一无所有。”肖培根说。但是肖培根颇有大将风度,胸有成竹。他首先聘请楼之岑、诚静容等专家做普查工作的兼职指导老师;其次,确定以中药材的“常用度”为普查的主要范围,指明任务方向。所谓“常用度”,就是重点抓500至600种常用中药,抓住了这个大头,就等于抓住了全国70%至80%的中药资源;第三,学中干,干中学,边干边学,上“实践大学”。
肖培根根据每个人的特长,把药物研究所药用植物研究室的年轻人派到全国各地中药材“常用度”高的产区。他自己则带头选择了资源相对比较多、工作量大的东北地区。缺少中文资料,他就随身带着仅有的几本日本早期出版的图谱,转战东北长白山、大兴安岭等地。
那时候的大学生可谓凤毛麟角。但是肖培根从来都是以学生的姿态,向经验丰富的药农、中药师傅虚心求教。一个来自“中央单位、肩负国家任务”的大学生干部,他的虚心与诚意,打动了每一位药农、每一位中药师傅的心。药农和中药师傅们纷纷把自己“压箱底”的绝技倾囊相授,这让肖培根掌握了许多书本上没有、在实践中行之有效的“绝活”。
1959年,全国第一次中药资源普查工作圆满结束。肖培根向国家交出了合格的答卷,对我国常用中药资源的地域分布、品质优劣、大致产量、存在的问题、解决的建议等,均进行了准确翔实的表述。这是中国近代中药资源最具权威价值的普查报告,其准确可靠的数据成为新中国中药资源宏观管理的科学依据。肖培根迄今已经指导了全国第一至第四次中药普查工作,为中药资源的管理保护和利用,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当全国第一次中药普查进入尾声时,全国掀起了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热潮。在全所讨论如何“献礼”的会上,肖培根大胆地提出:利用中药普查的成果资料,编写新中国第一部《中药志》。
《中药志》采用了肖培根他们自己设计的体例,包括哪些属于常用中药、次常用中药,哪些是很少用的中药,目标是集中整理研究全国的常用中药,同时还要介绍其本草历史。古代什么时候开始用的,应用的沿革怎样?它的原植物有多少?它的药材形状、组织,有宏观的,也有微观的。化学成分明确的中药还要介绍其化学成分及传统疗效。最后,还有一个附注,讨论相关问题。这样一种设计体例,都是以他们自己的实验工作为基础完成的。比如,把采集的每一种原植物加以整理、鉴定,把每一种药材都做成切片,描述它的显微组织特征,从而得来一手资料。1962年,4大本、100多万字的《中药志》完整出版,不仅受到了国内药学界的高度重视,还赢得了赞誉。
20年后,肖培根组织全国专家修订出版了第二版《中药志》。40年后,古稀之年的肖培根像重新梳妆打扮自己的儿女一样,于2002年修订出版了第三版《新编中药志》。40余年,3个版本,滋养着几代中医药人才的茁壮成长,体现出肖培根等老一辈科学家严谨治学、精益求精的科研态度。
国家的“中药大使”
1963年3月,肖培根作为专家被派往西非的加纳、几内亚、马里和摩洛哥4国考察访问。这一年,肖培根31岁,第一次出国,职称是助理研究员。与其同行的是业界知名的蔡希陶和陈封怀教授。一行三人,由蔡希陶任团长。那时出国的人很少,《人民日报》还把这件事作为重要消息发表。
这次出访,受到了大使馆的热情接待。每到一个国家,大使都亲自接待。第一站是加纳。到达阿克拉后,黄华大使不仅亲自接待,还介绍了当地有名的医生安朴福与他们进行业务交流。显然,黄华大使提前做了很多“功课”,这让肖培根非常感动。
初访西非4国,代表团除了在非洲考察当地的植物资源和药用植物资源,还为我国南方的植物园采集了很多重要的药用种子和经济植物种子,如古柯、毒毛旋花子、萝芙木、猪油果、牛油果、奇异果等,大约有200种。这批珍贵种子,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的海南、云南试验站以及云南热带植物园等地引种成功,在南方各地落地生根,造福着亿万中国人民。
由于殖民主义的统治,非洲草药受到很大的摧残。比如,在访问埃及时,开罗只有一家比较大的草药店。因为在英国统治时期,草医、草药是不合法的。在考察阿尔及利亚之前,卫生部部长专门向考察团求助,表示他们现在的草医只剩几个人,并且年龄已经70多岁了。一旦这几位草医去世,该国草医的传统经验就要失传了。其间,肖培根还肩负了两次“特殊使命”。
1974年,肖培根到埃及考察草药,同行的还有他的同事傅丰永教授。当时,我国驻埃及大使是著名的外交家柴泽民。他亲自接待并为考察团做了周密安排,使考察任务得以顺利完成。回国前夕,柴大使说:“你们暂时先不要回国了,在埃及待命,还有更重要的工作等你们去做。”
几天后,“特殊使命”下达——帮助坦桑尼亚整理研究该国的草药。一路上,肖培根很有压力。因为事前没有做一点儿准备,考察后必须要上交报告。“我就把当初在东北调查时采集标本的干劲拿出来了,把坦桑尼亚有关草药的资料进行了一次突击式整理,很快就掌握了坦桑尼亚大致有什么草药,接着就和当地的科学工作者分赴各地考察。”肖培根说。
考察团深入到坦桑尼亚穷乡僻壤乃至撒哈拉沙漠边缘。那里温度非常高,高到把鸡蛋放在外面,很快它就能被晒熟。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跟当地的陪同人员详细了解了每种草药的功效,还访问了很多草医,将资料汇总起来后,收获颇丰。考察团提交的报告,被世界卫生组织分发到各成员国,说中国帮助这些落后国家整理当地丰富的草药资源,是南南合作的典范。考察团回国抵达北京时,上述非洲国家的使馆参赞亲自到机场迎接。
第二次“特殊使命”是在1992年3月。当时中叙达成协议,由中国援建一个生产本地草药的小型制药厂。叙军方希望用本国的草药资源,解决部队一部分药品的自给。肖培根是担负这个“特殊使命”的不二人选。他对北非、中东地区的草药资源非常熟悉。
“到了大马士革后,接待我们的全是穿军装的叙利亚军方人员。在叙方的有力配合下,考察任务很快得以出色完成。根据部队里的常见病和多发病,我们选择了10多种产量很大的地方草药,用‘袋泡茶’的剂型进行生产。”肖培根说。
叙方和我国大使馆对这项工作十分满意。
1979年,肖培根作为新中国第一个技术官员,被派到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WHO)总部工作,负责世界药用植物名录编制等工作。1980年,他又被任命为WHO顾问,每年都去日内瓦WHO总部工作一段时间,主要是整理全世界药用植物的资料。
肖培根在日内瓦WHO总部工作,工资以“天”计算,包括旅馆费、交通费、伙食费等,每天至少有120美元,月底到银行领取。按规定,他可以住四星级宾馆,也可以每天往返乘出租车。那时,我国驻外人员凭发票可以实报实销。但他估算,在宾馆睡一个晚上,等于花掉自己在国内的数个月工资。因此,他吃住都在使馆,处处节约,前后节省了4万多美元,全部交给了国家。因为这件事,他受到了国家的表扬。
药用植物亲缘学的诞生
药用植物亲缘学是肖培根历经50余年,创建、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学科。提起往事,他语重心长地说:“这个讲起来可以用4个字总结——感触良多。那个时候,新中国刚刚成立,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了物资禁运,凡是包含进口药代用品的一律不准向中国出口。怎么办呢?那时我们刚大学毕业,国家交给我们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寻找能够替代进口药的国产资源。一个最简便的办法就是寻找和进口药最接近的药品。”
以肖培根为首的年轻人,奔赴全国各地,风餐露宿,不舍昼夜地努力,很快就找到了替代利血平的萝芙木。随后,阿拉伯胶、安息香、胡黄连等药物的代用品也被找到。
20世纪50年代初,全国第一次疾病防治大会上发出了“让高血压低头,让肿瘤让路”的豪迈誓言。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正是利用萝芙木,冲破了国外的封锁,研发出物美价廉的降压灵。阿拉伯胶是一种安全无害的增稠剂,能在空气中自然凝固,曾是食品工业中用途最广、用量最大的水溶胶。胡黄连为玄参科多年生草本植物,与黄连名称相似,同为治湿热泻痢之良药。但胡黄连善退虚热除疳热,而黄连则善清心火、泻胃火。安息香主治行气活血、止痛。民间常用的苏合香丸、至宝丹等都离不开安息香。这些原产于阿拉伯、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地的常用药材,短短数年就被肖培根等人寻觅到取之不尽的替代植物,打破了西方国家的封锁,满足了全国人民的需求。“在药用植物界,相似的药材有相似的成分和相似的活性。从这里,我找到了最初的灵感。”肖培根说。
肖培根视野开阔、博采众家、触类旁通,成为最早将计算机引入中草药研究的药用植物专家,并且在中国第一代计算机上展开了药用植物亲缘学的研究。
“在长期的药用植物研究中,我发现在某一个植物类群中,它们的植物形态、化学成分和疗效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如果再通过计算机和数学模式对这种相关性进行整理发掘,就能够寻找出很多规律性的东西。因此,在以后的研究中,我逐步把重点由放在一个植物上转移到放在一群相似的、有共性的植物上。我研究过的类群有人参类、大黄类、乌头类、贝母类等20多个类群,通过研究类群能够发现其中的规律,再用数学模式进行聚类分析。当时,我使用的是国产第一代计算机(国产6912型),因此必须采用打孔的方式输入各个传统疗效数据。”肖培根说。
1978年,《药学通报》终于复刊了。肖培根的重要论文《植物亲缘关系、化学成分和疗效间的联系性》在《药学通报》上发表。当然,它标志着孕育20多年的新学科诞生了。
药用植物亲缘学是应用性非常强的新学科。肖培根在上述论文中论述了五个方面:一是扩大药用植物资源方面的应用;二是在寻找进口药的国产资源方面的应用;三是对中草药的质量控制、鉴别和扩大药源的应用;四是帮助预测中草药中的化学成分、有效成分以及协助成分的鉴定或结构测定的应用;五是整理总结中草药的经验和指导新药寻找方面的应用。
2005年,由肖培根指导的“中国重要药用植物类群亲缘学研究”重点项目,通过了专家评审和基金委的批准。2010年年初,该项目在由国家基金委组织的重点项目验收中获得好评。该项目的圆满结束,标志着“药用植物亲缘学”作为一门新兴综合学科,具备了比较完善的学科体系。2015年,是药用植物亲缘学跨越发展之年——从形态分析转入分子遗传学研究阶段。同年7月,肖培根与郝大程、顾晓杰的合著Medicinal plants:chemistry,biology and omics,由英国著名的伍德海德出版社出版;同年9月,肖培根与郝大程合著的《药用亲缘学论纲——知识谱系、知识论和范式转换》,发表在《中国中药》杂志第40卷第17期上(3335-3342),阐述了药用植物亲缘学在现阶段更需要与“组学”结合,应用现代分子生物学的成果,探讨“亲缘-成分-疗效”间存在的规律性。
来源:《中国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