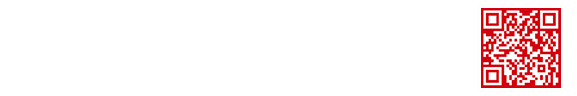时常,莫名地想一个词:隐匿。不是隐逸,后面这个词,属于不食人间烟火者。
“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这境界,不是容易抵达的。虽然这个季节,大地开始行动,删繁就简,摧枯拉朽,斩草除根,让一切呈现最初的模样,但是也掩盖了一些真相,让你比雾中看花、水中望月更难。
想等一场寒风来。寒风,在遥远的西伯利亚,在朝中原奔来的旅途上。隔着的光景,不过一两个月。可以想象得到,陪伴寒风的,是刺耳的啸声和没有感觉的冷。
没有感觉的冷,一直蛰伏着,在某个隐蔽的角落。有时候想,在中原这个小城,蜷缩在自己的住处,像接近冬眠的蟋蟀,收藏起所有的情感,把软软的身躯隐入泥土下的黑暗,琢磨一些个性心情,可以纯粹些。可是,无法做到。
现在,人们的生活越来越简单,简单到独处是一种奢望。尘世间,你需要支撑的力量,你需要帮扶的手,你需要慰藉的心,包括一些阿拉伯数字。甚至有时候,连关手机的自由,你都没有。总会有人,千方百计,通过不同的信息渠道,把你捕获入网。除非,你的一切,彻底消失,肉体、灵魂包括思想,成为别人口中的羽毛,无足轻重,如呵出的一口浊气。
于是,无来由地,心情无比恶劣,觉得没有感觉的冷,像一条无比恶毒的蛇,时不时地暗袭,甚至会让你趔趄一下。
秋深,叶黄。不知是不是老了,睡不着的夜里,总想复制曾经的轨迹。在属于一个人的夜里,拖着咳嗽的身躯,坐在电脑桌前,在因盗版软件导致的黑色屏幕上,写些不知所云的字。夜太冷,心也凉,同时弥漫的,总有缕缕忧伤。往往,你眼中的神圣,认为渗入骨髓与灵魂的事情,在别人看来,充其量不过是一些堆砌的文字,来宣泄一己的悲欣。
曾经有段日子,生活在自我封闭的生活中,放纵自己,麻醉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又懊悔得要命,就渴望来一场雪,用纯洁的白色,覆盖尘世间所有的污垢,以最初的姿势,等待。可是,身不由己。零零碎碎的东西,填埋在心里,植下坚强的根系,难以根除。
那个正午,到城边的一个单位办事。风在树梢上飞舞,整个田野苍茫一片。远远地,就看到好大一片草垛。云朵下面,村庄周围,麦垛铺展着、延伸着、成长着。无法看清楚草垛的表情,但从它们的个头上,体味得出农人曾经的忙碌。这些草们,等水分被空气吸干,当绿色被阳光掩盖,给人的,是一种无限的怀念,是无法企及的惆怅。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在哲学的范畴内外,人类与青草,都有同样的意义。这是我们共同的宿命。
想想,还不如一只鸟。
天空中出现一群候鸟,盘旋在草垛的天空,一个挨着一个,自由地飞翔,保持着足够自由的翅膀。没想到,在这里,竟然出现那么多精灵,不期而至。在城市的边缘,哪里有草垛,是属于我们自己的?真的,我们有时候,还真不如一只鸟儿,那样自由。
于是,想起一首诗:当我说到了饿/你就为我献出粮食/当我说到了冷/你就献出了火 而当我说到怕/我就可以在你身上打洞/安放我单薄的童年 我爱着你爱着你/这麦子忠诚的前世/爱着你这温暖的尸骸……
这首写给草垛的诗,记不起来,是从哪里看到的。想起来,心却一直慰藉着,仿佛在其上飞翔的鸟儿,寻到了自己的方向。
草垛里的草们,静默着,一句话也不说,深入着这个世界。它们平静地生活,不论面对日月,无论面对霜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