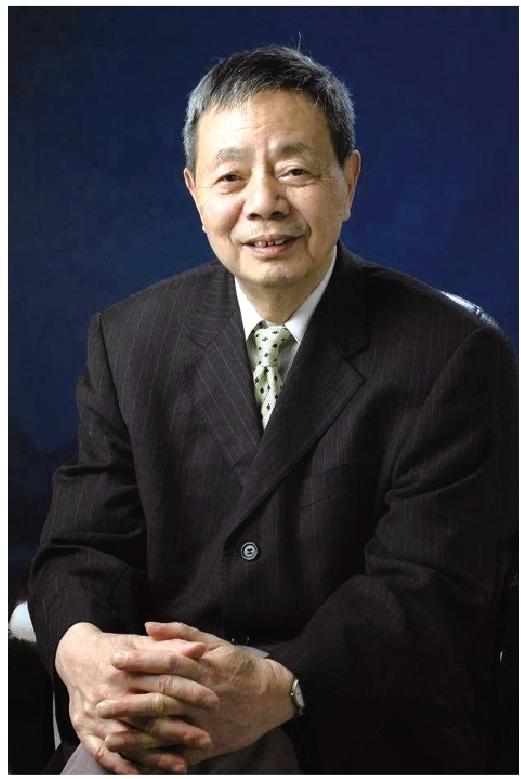半导体功率器件,是电能/功率处理的核心器件,更是弱电控制与强电运行之间的沟通桥梁,在“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型过程中,在民族电子信息产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陈星弼院士为此付出了几十年的心血。
闯出新路
陈星弼与功率器件的缘分要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那时,他作为出国留学人员赴美国俄亥俄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访问学者。
一个极具科研价值的问题吸引了陈星弼:以毫米为单位的小小芯片从晶圆片上划分而来,被制作成各种产品,但是每个芯片都有边界,它对功率器件的性能影响如何解决呢?
凭借扎实的功底和勤奋学习,陈星弼提出了一个独特的思路:应该有一个最佳的电荷分布,能在表面以最短的距离使击穿电压达到尽可能高的值,即最佳表面变掺杂。
“邂逅”功率器件,擦出火花后,陈星弼并没有顺着这条新路走下去。他犹豫着,要不要回到自己最喜爱的物理学研究领域?但归国后,陈星弼强烈感受到,半导体功率器件对国家电子信息领域发展的重要。于是,他放弃原来的理想,全力投入这一领域的研究中。
万丈高楼平地起,面向全新领域,陈星弼开始一砖一瓦搭建基础平台。1983年,他推动建立了微电子研究所,带领大家忘我地投入到科研工作中。每天晚上钟声敲过12下,学校要关门了,陈星弼才肯离开实验室,一路疾走,回到家中继续干。有时工作到凌晨两三点,有时通宵达旦,直到东方发白,他才短暂休息几个小时。
此时的陈星弼已年过五旬,却以比年轻人更勤勉的态度、更旺盛的精力投入到这一全新的事业中。于是,一条新路,在陈星弼坚实的步伐中,延伸向希望的远方。
陈星弼的几篇论文《P-N结有场板时表面电场分布的简单公式》《突变平面结表面电场的近似公式》等相继发表,“功率半导体器件及高压集成电路”这个崭新而陌生的词组从此与他紧紧联系在一起。1987年,微电子研究所的课题达到10个,经费将近30万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尤其值得高兴的是,‘半导体器件与微电子学’高分通过了博士点申请。”1989年11月,时任电子科技大学校长的刘盛纲院士,在一次校内会议上通报了学校参加全国第四批学科点评审的情况。陈星弼舒心地笑了。
勇攀高峰
“集成电路为电子信息时代奠定了基础,就像造房子一样。网络、云等都是重要的,但基石是微电子。”陈星弼曾这样介绍他的研究,“关于电子信息的发展,有两个重要的问题:一个是如何发现新的发电方法,比如太阳能电池;另一个是如何节省电能,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节省电能。”
陈星弼以微电子研究所为“根据地”,带领一批优秀的科研工作者在半导体功率器件领域不断奋斗,在中国首次研制了VDMOST、IGBT、LDMOST、MCT、EST等器件,并首次提出了各种终端技术的物理解释及解析理论。他想,人们希望功率器件耐压很高,接通时电阻很小,但它却有硅极限。如何实现突破呢?
陈星弼研究了很多终端技术理论,逐渐形成了表面耐压层结构的想法。他不分白天黑夜地泡在实验室里,甚至自己出钱租设备。助手唐茂成和叶星宁协助他到沈阳电子部47所投片。经过多次试验,陈星弼和他的研究小组终于通过改变功率管的结构,实现了复合缓冲耐压结构(现称为超结器件)。
超结器件导通电阻低,易驱动,速度快,引起学术界和企业界很大反响,被称作“功率器件的新里程碑”。
陈星弼对超结器件仍不满意,耿耿于怀的是它的缺陷。2000年后,他又发明了高K电介质耐压结构、高速IGBT、两种多数载流子导电的器件等,这使我国高压(功率)集成电路在一个新的起点上起飞。
科研人生
陈星弼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走上这条“幸福”之路的。那时,他刚从同济大学毕业,在南京工学院电机系任助教,后来又北上中科院进修。他被漂移晶体管吸引住了。漂移晶体管在当时是新兴事物,正逐渐替代饱和晶体管。
陈星弼利用假期进行推导。不久,他的第一篇论文《关于半导体漂移三极管在饱和区工作时的储存时间问题》发表在1959年的《物理学报》上,这是国际上首次指出集电区中少数载流子存储效应对开关性能影响的重要文章。
结束在中科院的进修后,陈星弼来到巴蜀大地。此时,交通大学(现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的电讯工程专业西迁成都,合并创建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现电子科技大学,简称成电)。陈星弼把对祖国的深情和对科研的热爱都融入这所新学校的建设之中,开始了他60余年的成电生涯。
在陈星弼的努力下,成电于20世纪70年代接到研制硅靶摄像管的科研任务。硅靶靶面研制小组成立后,陈星弼做了理论论证,提出工艺和测量方面进行攻关的3大难题。全组人员经过4个月的艰苦奋战,在733厂和970厂的配合下,终于研制出我国第一个硅靶摄像管。
在测量半导体的电阻率时,陈星弼发现了一个问题。平时,最常用的方法是“四探针法”,通常所用的理论计算方式必须假设均匀材料,陈星弼却发现实际情况和假设有差别。这一问题激发了他强烈的研究欲望。他利用业余时间研究电阻率,最后利用传统的电荷镜像法,颇具匠心地创造了一种在一维方向介质是不均匀的镜像电荷的方程。
从漂移晶体管到硅靶摄像管,再到后来的半导体功率器件,陈星弼一直葆有对科研的无限热爱和克服科学困难的壮志雄心。他曾说:“科研之初,就像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的第一乐章,我们挣扎、追寻、研究和争辩,内心有苦也有乐。然而通过不懈努力,终于克服了种种障碍,并且在某项研究中取得成功,这又像《命运》交响曲的第四乐章。”
立德树人
“严字当头,把学生当‘敌人’。”这是陈星弼几十年的教学感悟。他认为,讲授真学问的关键在“严”,把学生当作“敌人”,以难题驱动,进而提升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
陈星弼经常举一个例子:前中国女子曲棍球教练金昶伯,对待他的队员就像“敌人”一样,通过魔鬼训练让她们磨砺进步。正是在金昶伯的率领下,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一跃成为一个世界强队。
如何做到严格要求呢?陈星弼的方法是自主设计难题,让学生在攻克难题中提升能力,并不断创新。他还通过在考试题目中设置难题,辨识学生的学习成果差异,让分数“高斯”分布。
同时,陈星弼也非常重视“宽严相济”。他认为的“宽”,是指老师要引导学生加强基础课的学习,打下宽厚基础,奠定未来研究工作的基石。
着眼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陈星弼曾呼吁:“大学教育培养的不只是高级技师,而应以输出对科技发展有贡献的科学家为主,因此要站在对学生及中国高等教育高度负责的立场,加强基础课的投入,提升基础课的教学水平。”
无论工作多么繁忙,陈星弼都把教学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他曾主动请缨,接手“人人讨厌上”的量子力学,还为研究生开设了《半导体器件物理》《半导体器件的数值计算方法》《功率MOS》等新课。
课程很难,陈星弼却很兴奋。他曾说:“越伟大越深奥的东西我越喜欢攻克。”陈星弼的课保持着一贯风格:突出物理概念,启发式教育。
为了锻炼学生的英语能力,陈星弼在研究生课堂上采用全英文教学。他崇尚自由包容的课堂氛围,允许学生随意提问。讨论时,没有权威,没有师生关系,只有平等交流。学生们踊跃发言,甚至为某一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
陈星弼还经常给学生们开人文讲座,建议他们读世界名著、听古典音乐,锻炼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他认为,通识教育虽不能让人才速成,但从长远计,接受通识教育的学生的创新性和贡献更为突出。
陈星弼是严师,更是慈父。他掏钱请学生们看电影、吃饭,在甲型流感暴发期间自费购买中药熬给学生们喝。
更有意思的是,“让我付钱我才去”成为陈星弼和毕业学生聚会的“标准”。学生们都记得,有一次聚会大家偷偷付了钱,陈老师很不开心,批评他们“说话不算数”。下次再约时,陈星弼说:“除非我把上次聚会时的钱出了,否则我不去。”
2018年教师节前夕,陈星弼与刘盛纲、李乐民3位院士共同获得“成电立德树人成就奖”,这是属于电子科技大学教师的最高荣誉。
家国情怀
“只有科学和教育发展了,国家才能振兴。没有科学教育,国家就会落后,落后就要挨打。”在纪念二战胜利70周年时,陈星弼曾谈到科教兴国的意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在无形中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任何人不能阻止历史的车轮。”
这样的感悟与陈星弼刻骨铭心的少年经历密切相关。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1937年,战争阴云密布,不到7岁的陈星弼跟随父母离开上海,在连天的炮火中,踏上向西的逃难之路。
他们逃到了余姚、浦江,又辗转至萧山、金华、南昌、长沙、九江……历经艰险到达重庆,一家人才稍作安顿。陈星弼转学4次后结束了小学生活。
1943年,陈星弼转学到江津县国立九中。此时,“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大规模征兵运动正在全国开展。他唱着《棠棣之花》送别穿上戎装的同学,只恨自己年龄小不能参军。
年少的陈星弼在紧张的课余时间认真军训,操练、打靶,一丝不苟。语文老师教大家毛泽东的词《沁园春·雪》,他非常喜欢。陈星弼和同学还排演曹禺、田汉、夏衍、郭沫若的爱国话剧。
年岁渐增,陈星弼对祖国的爱更深,为祖国奉献一生的意愿更加强烈。大二时,陈星弼放弃了奖学金。他想,国家还有许多急需用钱的地方,自己也要为祖国尽微薄之力。毕业分配填写志愿表时,他在每一个志愿栏里都填上“服从组织分配”,并真诚地表示要到东北去、到西北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建功立业。
50岁时,陈星弼走出国门,以真才实学赢得了国际友人的尊重。为了给工业发展作出切切实实的贡献,他痛苦地放弃了关于理论物理的梦想,在功率器件领域艰苦工作,经常通宵达旦。
陈星弼视名利如浮云。他衣着朴素,不了解的人很难想象,这位看似普通的老人,发明的专利成果带来的经济效益约有20亿美元。
从大学时代开始,陈星弼就阅读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著作,还阅读了德国古典哲学著作。
终其一生,马克思主义给予陈星弼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能够在短促的人生中,以科学服务人类,这就是陈星弼追求的价值。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