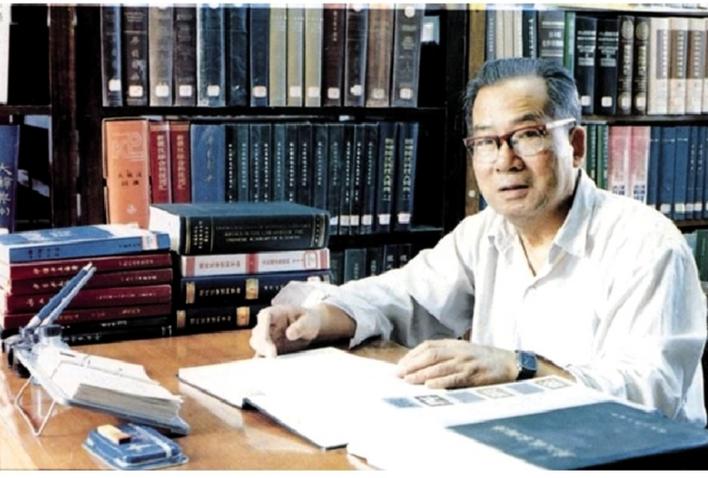他长期从事土壤、土壤侵蚀、水土保持和国土整治研究,提出华南红壤主要是古土壤和红色风化壳的残留以及红色冲积物的堆积,而不是现代生物地带性土壤的观点;他对黄土和黄土高原的形成提出了风成沉积的新内容和风成黄土是黄尘自重、凝聚、雨淋3种沉积方式的融合体;他还提出了整治黄土高原国土和根治黄河水患的“28字方略”。他是我国土壤学与水土保持专家朱显谟。
发愤图强的农村娃
1915年12月4日,朱显谟出生在隶属于江苏的崇明县海桥乡三光镇。1922年,朱显谟就读于三光镇初小。1925年,朱显谟初小毕业后,因当地没有高小,失学在家务农,农闲时到邻近的私塾旁听。次年,在初小老师的推荐下,朱显谟进入名为“协进小学”的高小读书。自此,他每天起床后自己做饭,来回步行10多里路去上学。
1929年,朱显谟考入崇明县的私立三乐初级中学,开启住校生活。在这所校风严谨的学校,朱显谟学习了国文、英文、数学、物理、化学、自然、中国历史、中国地理等课程,还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公开演出。节假日,朱显谟回到家中帮父母干农活。其间,他深深感受到农民的劳累和辛苦,从而产生了利用科学知识增加生产的想法。
1933年,朱显谟考入著名的上海中学。高中的课程难度很大,大部分科目采用英文教材,这对从农村初中出来的朱显谟来说是个挑战。他加倍努力,将所有精力都用在功课上,成绩提升很快。在所有科目中,朱显谟尤其喜欢数学,不仅白天思索,甚至晚上做梦还在解题。朱显谟的数学老师朱凤豪是当时的名师,对他关爱有加,希望朱显谟能考取上海交通大学。但朱显谟却自有志向。高考前朱凤豪来到朱显谟的宿舍,了解他报考的大学。朱显谟答曰:“中央大学农学院。”朱凤豪听后,说了两个字:“包取。”不久,朱显谟在上海中学的毕业生纪念册上,毅然写下了自己的理想——“将来当一名科学农民”。
大学里的“实验大王”
1936年,朱显谟同时考取了中央大学和浙江大学,因叔父朱济明在中央大学工作,便选择了中央大学,进入农学院农业化学系学习土地肥料专业。
在校期间,朱显谟是一个“努力读书,不问政治”的学生,很少参加学生活动,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学习和实验上。
令他记忆深刻的课程是罗宗洛先生教授的植物生理学。罗先生从不照本宣科,而是列举各家所长,一一加以评比,有时也结合自身实践加以论证,这大大激发了朱显谟的深度思考。
大学期间,朱显谟最感兴趣的是做实验。他经常打破作息时间,在实验室专心进行化学分析实验和农产品制作。有一次,他独自实验获得了味精的白色晶体,受到了老师的表扬,并被大家称为“实验大王”。这些经历让他明白了亲身实验在获取知识过程中的重要性,也让他开始不再迷信书本知识。
1940年,朱显谟在植物生理学家陈方济的指导下,完成了毕业论文《土壤钾质固定问题之探讨》,获得了农学学士学位。
探索红壤引争议
毕业后,朱显谟参加了江西省地质调查所的录取考试,与同班同学吴本忠一起被录取。因抗战影响,朱显谟先去位于重庆北碚的中央地质调查所报到,在该所土壤研究室接受了半个月的培训后,便在著名土壤学家侯光炯的带领下,奔赴四川铜梁,开始了野外实习工作。
这段实习经历给朱显谟后来的土壤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对其影响深远。
1940年,朱显谟到达位于江西省泰和县赣江东侧小塘洲村的江西地质调查所,开始在江西从事土壤调查、制图工作。在侯光炯的指导下,朱显谟完成了第一篇学术论文《冠朝圩区土壤》,发表在《土壤专刊》上。
当时,除了野外调查,朱显谟还进行相应的土壤改良试验。在进行野外调查的过程中,朱显谟发现江西省内红壤分布广泛,且酸性很强,除了临近水源的红壤区可以种植水稻,其他地方均难以生长农作物。因此,对红壤的改良是当时的一个迫切问题。在红土改良研究过程中,朱显谟认为添加客土和烧土作用最为显著,但当时这项工作未能得到重视,更谈不上普及。1950年,朱显谟在参加全国土壤肥料会议时,对江西省红壤的利用和改良作了总结报告。
那段时期,朱显谟一直不忘对江西境内的红壤成因进行思考。当时学界普遍认为红壤是江西的气候性土壤,形成于高温高湿的气候环境中。刚到江西工作时,朱显谟对此理论深信不疑。但随着一系列野外考察和实验,他对“生物地带性土壤”这一观点产生了怀疑。20世纪40年代后期,他根据积累的经验,明确指出华南红壤是古土壤、红色风化壳的残留和红色冲积物的堆积,不是地带性土壤,而且这种红化作用早在史前就已经发生。朱显谟开创性的观点引起了学界的巨大争议,他本人被斥为“离经叛道、标新立异”,但他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观点,而是“峭立原地任水过”。在后续的研究过程中,朱显谟利用新技术、新数据,从土壤侵蚀沉积学的角度,结合生物小循环、生物反馈等数据加以补充,证明自己的论断是正确的。后来,这一观点被土壤学界普遍接受。
结缘黄土,扎根西北
1947年,应中央地质调查所北平分所所长高平的邀请,朱显谟离开江西地质调查所,计划前往北平,但因北平战事,遂留在南京中央地质调查所土壤研究室工作。
1951年,土壤研究室在陕西武功筹建黄土试验站,朱显谟即奔赴西北黄土区,从此与黄土结缘。
1956年,中国科学院西北农业生物研究所成立(后更名为“中国科学院西北生物土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西北水土保持生物土壤研究所”等,1995年更名为“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以下简称水保所),朱显谟领导的黄土试验站并入该所并改名为“土壤研究室”。
考虑到工作需要,1959年,朱显谟放弃大城市的便利生活条件,举家迁入当时生活条件非常艰苦的西北小镇杨凌。当时,研究所的条件极其简陋,最开始连供电都无法保证,只能点蜡烛,后来才用上煤油灯。朱显谟分到了两间房子,每间
大约十几平方米。他从南京带来的书籍、资料、土壤标本,没有地方存放,只好把它们放在房间外的走廊里。但这些困难丝毫没有影响朱显谟在此干出一番成就。
1951年在甘肃陇东子午岭调查时,通过研究黄土剖面,朱显谟发现这一剖面具有一定的腐殖质,有明显的碳酸盐淋失、淀积和一定的结构、质地,还有一定厚度的过渡层,有时能见到填土动物穴和大小根孔与根系遗骸。因此,他认定这就是古土壤。
1954年秋,朱显谟在陕北韭园沟进行野外调查时,发现在黄土中有时可见以细沙为主的土层,呈色红晕,质地稍黏重,一般是粉沙黏壤土到粉沙黏土,厚度在1米左右。朱显谟将其称为“红层”,即现在统称的“红三条”。他在该年撰文,首次公开阐释了黄土剖面中的“红层”是古土壤的观点。1958年,经过几年的论证,朱显谟确认了红层是古土壤,并在《关于黄土层中红层问题的讨论》一文中指出,陕、山、甘的红色土中所夹的若干层呈色较红、质地较黏重的土层(即红层),其成因是风成的,其界属是古土壤层。
建立子午岭野外试验基地
20世纪50年代初,朱显谟刚来到西北考察时,子午岭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子午岭位于陕西富县,属于陕西与甘肃交界处,从汉至明,一直是重要粮食产地。明以后,因水土流失严重及战争影响,人类活动逐渐减少,植被逐渐得到恢复。朱显谟看到子午岭的森林草坡后,认为这就是黄土高原的希望。自此以后,他一直期望能在子午岭建立试验站。
1962年,朱显谟终于如愿在子午岭东坡的连家砭地区建立了野外试验基地,开始系统研究不同土地利用情况下土壤、土壤侵蚀以及植被的演变过程,探寻防止土壤侵蚀和改良植被的途径。
子午岭位置偏僻,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当时朱显谟带领试验点的工作人员,借住在附近一所小学,他们从杨凌自带卧具和生活用品,自己动手搭起灶台。由于交通不便,所里派车也只能把
他们送到子午岭附近,他们再背着行囊,步行20多公里进山走到试验站。而子午岭和外界的信息沟通也非常滞后,队员们大概15天才能看到一份报纸,晚上十几个队员共用1个油灯。就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朱显谟和试验站的工作人员一直坚持着。
对黄土高原地区土壤重新分类
中国的现代土壤分类始于民国时期。1930年,美国土壤学家梭颇带领地质调查所土壤室的研究人员,在中国进行了大范围的土壤调查,并以美国马伯特的分类体系,建立了2000多个土系。
20世纪60年代初,朱显谟根据自己的多年经验,在“以土为主,土洋结合和土中生洋”的基础上,研究出黄土地区主要土壤分类系统。该系统共分为11个土类、37个亚类、76个土组、168个土种。基于土壤的本质是土壤肥力,他认为自然土壤和耕作土壤可以统一分类,分类原则是将群众经验与现有理论相结合。这样既便于系统整理黄土地区的土壤,又容易被群众掌握,更能指出以后合理利用和定向培肥的途径。具体设土类(含亚类)、土组和土种(含变种)三级制。
朱显谟认为,土类应该兼顾生物气候的地带性和人为利用的功效,对自然区划和农业规划都要有益。亚类则根据水热条件和耕作制度等进行划分。对于土组的划分,朱显谟认为可以依据耕性,即土壤质地、结构性和累积情况而定,并支持采用劳动群众积累的丰富经验。对土种的划分,朱显谟仍然吸取了群众经验,以土壤肥力,即土壤相对肥瘦的差异作为指标。
黄土高原整治“28字方略”
20世纪80年代,在河北承德举行的黄河中游黄土高原水土保持考察总结会上,朱显谟发出了“群众生产尊规律,植树种草催河清”的呼声,引起参会代表的共鸣。会后,朱显谟总结了40多年来的土壤研究经验,结合黄土高原的具体特点
和当地群众的生产经验,提出了以“迅速恢复植被”为中心的黄土高原国土整治“28字方略”,即“全部降水就地入渗拦蓄,米粮下川上塬、林果下沟上岔、草灌上坡下坬”。
“继承模仿,突破创新”
朱显谟在总结自己的学术思维时,突出使用了“继承模仿,突破创新”8个字。他在早年的土壤学研究中,也是遵循经典,以经典为基础。例如苏联土壤学家威廉斯提出的“成土过程和风化过程同时同地进行”理论,曾是朱显谟进行土壤发生学研究的理论基础。但在多年的实践活动中,他越来越发现威廉斯理论的局限性。因为,威廉斯的理论仅适应于岩浆岩体(或块状石灰岩)上进行的与陆生生物相一致的原始成壤阶段。而在沉积岩体上,因环境条件的不同,成土过程和风化过程无论在强度上还是进程上,都会出现明显的差距,甚至形成一定的反差,又因着生生物的自然演替和人为生产等不同而产生根本性的变化。
在此基础上,朱显谟继续研究并得出结论:风化过程是细粒化和脱硅过程,即块状岩体经过热力作用变成细粒物质;原生矿物经过化学和生物化学作用而变成次生矿物和矿物元素的简单氧化物或可溶性盐类,其过程将完全受制于环境条件对脱硅作用的影响。朱显谟的研究不仅修正和发展了威廉斯的学说,还从研究风化过程和成壤过程的实质入手,进一步明确了这两个过程在土壤形成过程中的内在联系和各自的范畴,并总结为:一切地质大循环只能是土质形成过程,或称之为“成土过程”;而生物小循环才是真正的土壤形成过程,或称“成壤过程”。
朱显谟在多年的研究过程中,坚持自己的“尽信书不如无书”理念,学习书本上的知识,了解以前的测试数据,但不将其奉为“真理”,而是结合自己的亲身实践和独立思考,修正和拓展前人的理论,甚至自己的理论,以期获得最准确、客观的知识。
来源:《中国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