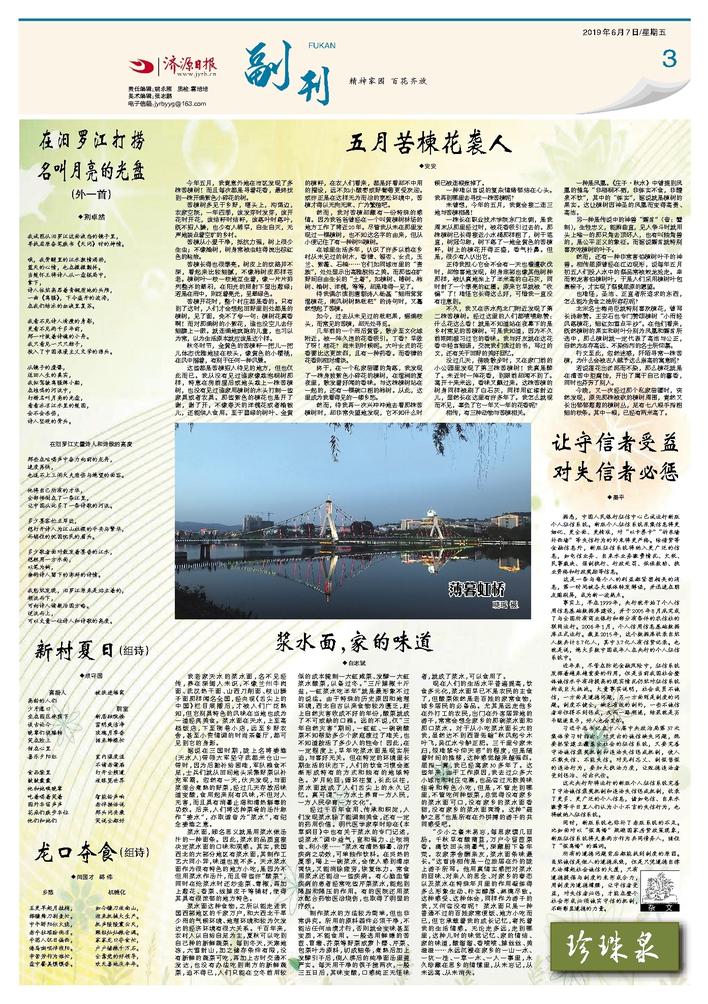◆白志斌
我老家天水的浆水面,名不见经传,养在深闺人未识,不像兰州牛肉面、武汉热干面、山西刀削面、岐山臊子面那样闻名全国,经央视《舌尖上的中国》栏目展播后,才被人们广泛熟知,但它别具特色的风味在当地也成为一道经典美食。浆水面在天水,上至高档饭店,下至街巷小店,远至乡野农舍,甚至小资情调的时尚茶餐厅,都可见到它的身影。
据说在三国时期,陇上名将姜维(天水人)带领大军坚守武都米仓山一带时,因为后勤补给困难,军队粮食不足,士兵们就从田间地头采集野菜以补充军需。忽然有一天,伙夫发现,与面浆混合煮熟的野菜,经过几天存放后味道变酸,食用起来别有风味,不但对人无害,而且具有消暑止渴和清热解毒的功效。后来,人们将这种菜肴的汤汁称作“姜水”, 亦取谐音为“浆水”,有纪念姜维之意。
浆水面,顾名思义就是用浆水做汤汁的一种面条。因此,浆水的品质直接决定浆水面的口味和观感。其实,我国西北的大部分地区有浆水面,其制作工艺大同小异,味道也差不多。天水浆水面作为很有特色的地方小吃,是因为不但用浆水作汤汁,而且带些许“酸菜”,同时在炝浆水时还炒韭菜、青椒,再加上葱花、香菜、线辣皮子等辅材,使得其具有很浓郁的地方特色。
浆水面这种食物,之所以能走进我国西部地区的千家万户,和大西北干旱少雨的气候环境、地理环境和较为欠发达的经济环境有很大关系。千百年来,农村人以自给自足为主,夏秋可以吃到自己种的新鲜蔬菜。每到冬天,天寒地冻,大雪封山,加之储存条件有限,没有新鲜的蔬菜可吃,再加上古时交通不发达,也没有办法吃到南方的新鲜蔬菜,迫不得已,人们只能在立冬前用较低的成本腌制一大缸咸菜、发酵一大缸浆水酸菜,以备过冬。“三斤辣椒十斤盐,一缸浆水吃半年”就是最形象不过的说法。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和地理环境,西北自古以来食物较为匮乏,赶上自然灾害收成不好的年份,酸菜就成了不可或缺的口粮。远的不说,仅“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一缸缸、一碗碗酸菜不知帮助多少个家庭渡过了难关,也不知道救活了多少人的性命!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早年吃浆水面是现实所迫,与喜好无关。但在特定的环境里长期生活的状态下,人们的饮食习惯会逐渐形成特有的方式和独有的地域特色。岁月轮回,循环往复,长此以往,浆水面就成了人们舌尖上的永久记忆。真可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民,一方人民孕育一方文化”。
经过千百年食用、传承和积淀,人们发现浆水除了能调制美食,还有一定的药用价值。明代医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有关于浆水的专门记述,说浆水“调中益气,宣和强力、止咳消食、利小便……”浆水有清热解暑、治疗疾病之功效,可单独作饮料。在炎热的夏季,喝上一碗浆水,会使人感到清凉爽快,又能消除疲劳,恢复体力。常食用浆水还能治一些疾病。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经常吃些芹菜浆水,能起到降脂和降压的作用。有的医院还用浆水配合药物医治烧伤,也取得了明显的疗效。
制作浆水的方法较为简单,但也非常讲究。所用的原料器件必须干净,不能沾任何油渍才行,否则就会变味甚至变质,不能食用。一般选用鲜嫩的苦苣、苜蓿、芥菜等野菜或萝卜缨、芹菜、包菜叶为原料,切成细条,煮熟后加上发酵引子后,倒入沸后的纯净面汤里盖严实。每天用干净的筷子搅两次,一般三五日后,其味变酸,口感纯正无怪味者,就成了浆水,可以食用了。
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饮食多元化,浆水面早已不是农民的主食了,但酸菜依然是老百姓的家常食物,城乡居民的必备品。尤其是远走他乡在外打工的农民,出门在外客居异地的游子,常常会想念家乡的那碗浆水面和那口浆水。对于从小吃浆水面长大的我,虽然达不到西晋张翰“秋风起兮木叶飞,吴江水兮鲈正肥。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禁兮仰天悲”的程度,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屈指一算,我已经离家30多年了。这些年来,由于工作原因,我去过众多大小城市和村庄屯寨,也品尝过无数美味佳肴和特色小吃,但是,不管走到哪里,不管吃何种饭菜,总觉得没有家乡的浆水面可口,没有家乡的浆水面香甜,没有家乡的浆水面爽滑。这种“莼鲈之思”也是所有在外拼搏的游子的共同感受吧。
“少小之餐未易忘,每思家馔几回肠。千秋早有酸蒲苴,万户今留苣菜香。痛饮田头消暑气,深藏厨下备年荒。农家茅舍酬亲友,浆水面条味最长。”这首诗相传是一位旅居在外的陇上游子所写。他用真情实感把对浆水的回味、对亲人的思念、对家乡的眷恋以及浆水在特殊年月里的作用凝练得多么形象生动、朴实醇厚、淋漓尽致。这种感受、这种体会,同样作为游子的我,又何尝没有呢? 浆水面只是一种普通不过的百姓家常便饭、地方小吃而已,但它承载着我的成长记忆,寄托着我的生活情感。无论走多远,走到哪里,这种儿时的味觉记忆、家的情结、家的味道,酸溜溜、香喷喷、辣丝丝、美滋滋……永远沉浸在家乡的一山一水、一坑一洼、一草一木、一人一事里,永久珍藏在思乡的情愫里,从未忘记,从未远离、从未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