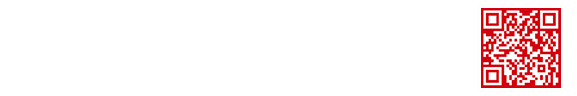◆赵长春
“小满麦渐满”,是说过了节气小满,麦子基本就成熟了,拿老家的话来说,就是经得嘴了,可以吃了。
老家还有一句话,五月端午吃新麦,是说端阳节前后,新麦就收割、归仓了,就可以磨面蒸馍擀面条搅面汤了。
麦子本身就是国人的重要粮食作物,承担着重要的责任和义务。所以,在过去青黄不接的日子里,小满一到人欢马叫。特别是作为上小学的正能吃的我们,对于可以吃新麦有着特别的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燎麦。
我们燎麦,就是掐几穗饱满的麦子,用细软的柴草燃起火苗,然后将麦穗来回迅速地移动在火苗中,燎。
燎,是一种火候的拿捏,伴随着或近或远的烤,是渐硬还软的麦粒在芒壳中与火的热情相遇,是半青的麦子吸附火的热烈后渐次为黄的“窑变”,是由青涩而香泽的华丽转身。
——这一过程很快很短,我们却能很好地把握,然后,吹去或者揉搓去芒壳,就可以让舌尖品味嫩、香、软、热、甜的麦子了。
燎麦的嫩、香、软、热、甜,多半在上学或者放学的路上体验,伴着一份被大人们发现而批评的惊险,特别严重的是老师的警告,从而多了一份神秘:燎麦,是小伙伴们的一种集体行为,需要分工寻找柴草、烧火、掐麦、放哨。大家就订立攻守同盟:“谁给老师说谁是小猪、小狗!”
但是,我们的伎俩总会被轻易识破,或者我们的同盟总会被轻易化解,总有人不时地被罚站、写检查,被没收火柴。小伙伴们互相猜疑而再团结再分裂再组合再被燎麦的滋味所诱惑,甚至不惜从盐罐里偷出盐,在作业纸上研磨为比较细碎的颗粒,撒在正被火苗燎烤的麦穗上或者吹去芒壳的麦粒上,于是就多了份香气、香味!
——那时候,我们是多么容易满足的孩子!对于大人们的苛刻,我们觉得特别委屈。后来才明白,大人们多么的不易:既心疼孩子又心疼麦子,承受着双重的折磨。
那时候,我们还嫉妒麦子的得宠比我们更多。在大人们的眼里,麦子甚至比孩子还重要,“再这样糟蹋庄稼,打折你们的腿”!
可是,我们不怕,我们读出了另一种感觉,从大人们的语言和表情的背后。
大人们看得严,没有火柴,上学或者放学的路上,我们就用另一种吃法:直接将揉搓掉芒壳的麦子捂进嘴里,嚼吸麦子清新的香,嚼着嚼着,就剩下了面筋,黏在舌尖上,旋来转去,技巧好的话,能吹出泡泡来!
霞姐吹得最好,将这种技巧运用得最自如。
霞姐比我高两个年级。一起上学的路上,她正吹着泡泡,碰见有人过来,会不动声色地将泡泡收回去,贴在腮帮内。
她说,可以将已经能吹泡泡的面筋给我,教我也吹出泡泡。她叫我张开嘴,要将面筋吐给我。我头一扭,转身后退——我才不呢,虽然我再怎么努力,也不能咀嚼出那样的面筋。
可是,和她同年级的顺哥想要。她又不给,一扭身,眼一瞪,书包一正,“滚蛋”!然后,“噔噔噔噔”,向前走了,麻花辫子随着壮实的腰身晃荡如风在流。
唉,他们这些大孩子的事,当时我不懂,有些遗憾……
布谷鸟叫了,又一个小满。人生中不再燎麦多年后的又一个小满,我在一块麦地前转悠,口袋里装了打火机,虽然我从不抽烟。我想掐几穗麦子,想燎出少年时代的滋味。
可是,总有人来往,还有几只鸟儿落下,冲我骨碌着水汪汪的小眼睛,仿佛一下子看穿了我的企图。
还有,霞姐不在,顺哥不在。在老家生儿育女的他们,已经是新的农场主了,流转承包了几百亩地,年年种麦,种花生,种苞谷,种棉花。
我羡慕他们有三个孩子:两个儿子,一个闺女。
我羡慕他们年年种地,有几百亩地,想种啥就种啥。我已经有足够的想象,想象他们在自己的地里如何恩爱,哪怕疯狂,虽然他们早已过了青春年少!
还是不燎麦子了。祝福霞姐、顺哥他们,祝福麦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