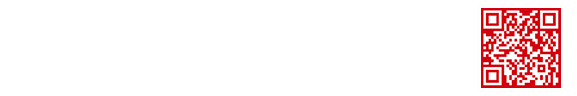暖暖的春风,吹过昆明上空,拂过蓬勃生长的植物。昆明北郊的植物园里,嫩绿的小草蓬勃茂盛,黄色的迎春、白色的玉兰,粉色的樱花,打着苞的山茶和或已油绿,或正换衣的各类植物一起热闹地描述着昆明春天的模样。
往东北行3000公里,是还在薄雾笼罩中的江苏扬州。如果芜园还在,那些熬过一冬的花草树木或许也开始在春天的节气中展眼舒眉了。
这是吴征镒一生中最值得记取的两个地方:家乡那个让他对植物万千奥秘产生最初好奇的芜园;成为一个植物学家后徜徉数十年从未离开的研究地。
家乡的芜园已在岁月更替中消失无影,但那些生生不息的花草树木还在,清晰如昨的植物卡片还在、承载着几代人心血的植物典籍还在、蓊郁苍翠的生态保护站还在、茁壮生长的橡胶林还在、星罗棋布的自然保护区还在……它们代表着吴征镒对自然的爱、对祖国的爱、对云南的爱、对科研的爱。它们以淡然且厚重的存在,诉说着吴征镒传奇的一生。
小小植物家
1916年,吴征镒出生于一个破落的封建大官僚地主家庭。年龄稍大时,他受教于私塾,读四书五经,打下了坚实的古文底子。10岁时,在父亲的小书房中,吴征镒偶然见到清代吴其峻的《植物名实图考》和牧野富太郎的《日本植物图鉴》,便痴迷上了植物,萌生了要穷其根本的念头。当同龄孩子忙于嬉笑打闹时,吴征镒却整日在家中荒废的后园——芜园中看花、看草、看叶、看竹。兄弟们不爱和他玩,说他没意思,呆呆的。可他不以为然,在芜园中掐“黄黄仔”、看竹笋破土、采榆钱儿、剥新鲜的豌豆吃。好奇春夏为何繁花满枝,而冬天却又叶落枝头……这一年中,吴征镒硬是靠着书本在芜园中认识了几十种树木花草,并开始在初中老师唐寿先生教授下采集制作标本、解剖花果,成为同学中有名的小小植物家。
随着对植物的深入了解,吴征镒日益觉得植物的大千世界难以穷尽。于是,才上初中一年级的他便立志,长大后要专攻植物学,将来有一天能走遍万水千山,把没看过的植物全看完。高中一年级时,吴征镒采集的标本得到了老师唐耀先生赞赏,唐耀先生专门为他在班上开了一个展览会。老师的鼓励、同学的羡慕,更坚定了他报考大学生物系的念头。
吴征镒成长的阶段,正是中国多灾多难的年代。他刚上高中时,发生了“九一八事变”;考上清华时,爆发“一二九”学生运动,接着又是西安事变;大学毕业后第一年,又是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和多难的国家一样,他也命运多舛:家道中落,生计多艰,清华4年学业,靠五哥资助完成;在联大当助教,也是饥饱相伴,清贫度日。苦难的岁月磨砺着他,也锻造着他。和所有信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热血青年一样,他亟愿投身报国,并立下了“科学救国”的志向。这期间,他除了关注课堂学习,还想尽一切办法开展野外植物调查。这奠定了他此后在植物地理分布观察方面集大成的基础。
大学毕业后,拿着每月80块大洋助教工资的吴征镒,参加了由段绳武发起组织的“西北科学考察团”,一路到大西北。正当他满怀激情地去认识中国时,“七七事变”的爆发,让他不得不半途折返老家扬州。此时,北大、清华、南开3校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吴征镒收到老师邀请,去临时大学任助教。1937年年底,临大迁往昆明,吴征镒开始和大家一起,历时68天,从长沙徒步越湘、黔至滇。
这半年,是吴征镒真正从书斋走向山野的开端。一路上,他观风景、悉人文、品世情、哀国运,既感怀河山之秀,又深憾时局之乱。一本“长征”日记,记述着他一路的所观所感。
1663.6公里,从长沙到昆明,吴征镒用脚丈量完了这片植物众多、景色秀丽的祖国南线土地。
求知报国心
在清华和联大,吴征镒遇到了对他日后影响颇深的3个老师:吴韫珍、闻一多和李继侗。闻一多因激进直言,讥讽当局无能而惨遭刺杀,这让吴征镒非常愤怒。这个一心扑在植物世界,只想科学报国的知识分子开始加入到学生运动中,并投身革命。1946年,吴征镒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由那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子成为一个敢为国家事鼓与呼的进步青年。而此时,并不知他真实身份的另一位老师李继侗却积极为他谋划着出国留学的事。看中这个青年的“慧”与“钻”,李继侗希望他能在国外接受更系统的教育。从联系哈佛大学到填写资料,老师都一手包办了。当吴征镒知道这一切后,陷入了深思:是留下来,继续投身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起见证中国的新生?还是去国外,学更多的知识后再回来报效国家?几经权衡,吴征镒最终选择了前者。
心中装着对国家的爱,吴征镒留了下来。他要么静心整理植物卡片,要么跋山涉水调查采集。这段时间里,他在用“洋油箱”堆成的简陋的标本室内,将没上标本台纸的标本,对照仅有的文献和秦仁昌所摄的模式标本照片,及自己几年来积累的昆明、滇西南等处的标本进行了系统整理;在中国医药研究所内,自写、自画、自印,与同事一起考证完成了《滇南本草图谱》第一集。
抗战胜利后,吴征镒参与科学院整理工作。几年间,他北上南下,做了许多工作,之后又重返昆明,开始了与云南近60年的植物情缘。
一张张植物标本卡一份份情
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球场边的石头墙上,“原本山川,极命草木”8个大字泛着光。每个路过这里的人,都会情不自禁地看上一眼。也许,他们当中并不是每个人都知晓这是吴征镒一辈子践行的探索草木本源的科研精神。
如果把吴征镒对植物的研究从幼时算起,那他在这个领域,已坚持了近90年。在吴征镒70多年的植物分类研究中,他定名和参与定名了1766个植物分类群,涵盖94科334属,是中国发现和命名植物最多的一位。以他为代表的三代中国植物分类学家改变了中国植物主要由外国人命名的历史。
儿时的好奇、青年时入门、成年后的痴迷,使吴征镒的一生都绘满了让人心醉神迷的绿色。曾经有人说,如果世界上有人能说出每一种植物的名字、了解每一种植物的习性,那么吴征镒一定是其中一个。如果世界上有人能听懂每一种植物的语言、理解每一种植物的情感,吴征镒也是其中一个。
吴征镒摸清了中国植物的家底,参与组织了《中国植物志》的编纂,为中国土地上的一草一木建立了户口本。这部植物学巨著历时45年完成。吴征镒和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华南植物研究所、昆明植物研究所等单位共同努力完成了全套著作2/3以上的编研任务。第一卷要概括已出版的前79卷的成就,最难写,是由吴征镒亲自承担的。此外,吴征镒还主编完成了《西藏植物志》和《云南植物志》。
选择科研,就是选择寂寞。吴征镒没有一天远离过植物,放弃过植物学研究。
从1940年到1950年,吴征镒用整整10年的时间,对照老师吴韫珍抄来的中国植物名录文献及秦仁昌拍摄的照片,整理和鉴定了3万多张植物标本卡片。这些卡片,成为后来编撰《中国植物志》《中国高等植物图鉴》最基本的素材。
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可以坐10年的冷板凳,做一件没有人做过、也少有人关注的事,这得需要多大的兴趣和毅力?对此,吴征镒却说:“栉风沐雨、饮饿劳顿、板凳硬冷、默默无闻,对我来说都是快乐的。快乐,使我有充沛的精力完成吴韫珍先生的夙愿。”
“摔跤冠军”
西双版纳是云南植物种类最多的地方,也是吴征镒学术考察最频繁的地方。每逢雨季,热带雨林的红土地一片泥泞,走在上面的人常会打滑。吴征镒是扁平足,走久了会摔跤。另外,他行走时只看植物不看路,经常在红泥巴路上摔跤,弄得全身满是红泥。在大围山考察,他也是一路摔着跤完成的。因此,大家送了吴征镒“摔跤冠军”的雅号。
这个雅号也让吴征镒颇有收获。中科院院士周俊曾同吴征镒一起考察文山西畴的植物,吴征镒在密林里摔了一跤,坐到地上迟迟不起。“我还以为他伤哪儿了呢,正想去拉他,却见他左顾右盼,突然看见一株白色寄生植物,立刻拿在手上仔细察看,认出是锡杖兰。他欣喜地叫大家‘快看快看,这里有个植物,是中国的新纪录’。”周俊说,这个摔出来的“重大发现”,多年来一直是同事们口耳相传的佳话。
玻璃瓶里的榴莲种
位于云南的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中,有一个很特别的大玻璃瓶,瓶里装着一把榴莲种子和半个榴莲壳,瓶上贴着标签:吴征镒院士赠。这是在种质资源库刚建起来不久,吴征镒秘书送来的,说是刚吃完的榴莲,特意把种子留着,希望给种质库添一点内容。
选择回到云南,对吴征镒来说是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近60年的岁月,他和草木相亲,与云南同行。即使是在“文革”期间,他也从未走出植物的大千世界。1970年,全国兴起大搞草药运动。被分配去烧开水炉的吴征镒知道了,千方百计想做一点有用的事,发挥一技之长。劳动之余,他为云南省中医中药展览会展出的中草药进行学名订正。一个偶然的机会,吴征镒得到一本“赤脚医生”使用的中草药小册子,非常高兴,就请朋友帮他收集这种小册子,以便对各地的民间常用中草药植物进行订正。他一边在“牛棚”烧开水,一边摘抄小册子上的内容,凭着惊人的记忆力,把中国的几千种中药、草药,按低等向高等的演化次序,编出了详细的目录,并把植物名称和中草药名称统一起来,在古代医书及植物学有关书籍的记载中进行考证。在考证中,他发现很多名不见经传,或在经传中已经失传的中草药植物。两年间,他整理记录了4大本关于各地中草药植物的笔记。这后来成为编辑《新华本草纲要》的可靠依据。“文革”期间,吴征镒白天在昆明郊区的黑龙潭田间锄地时,记下看到的各种植物,晚上回到小屋后赶紧悄悄写出来,并把它们进行归类。就这样,他完成了9万字的《昆明黑龙潭地区田间杂草名录》。
近60年来,他用一个植物学家广博的胸襟和执着的坚守关注着云南,让云南的植物为天下所知,让中国植物分类学的研究从云南走向全世界。
再不看,就没时间了
成长于时局动荡的年代,吴征镒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实现其踏遍千山万水,找寻中国植物的梦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觉得已耽误很多时间的吴征镒,在这来之不易的宝贵年华里分秒必争,恨不得把所有的时间用于科研。他马不停蹄地行走于中国的大江南北,高原河谷。花甲之龄时,他还一次次到西藏、新疆等地考察,在喜马拉雅山的雪峰和塔什库尔干的沙漠里留下了足迹。80岁高龄时,他还去台湾考察植物。吴征镒4次进藏,最终出版《西藏植物志》。
1956年,前苏联专家来云南考察。在德宏,他们对从未见过的亚热带植物惊叹不已。更让他们惊叹的是,无论把手指向哪种植物,吴征镒都能迅速地报出这种植物的拉丁名。苏联专家送给他“植物电脑”的美誉。在英国大英博物馆,英国科学家拿出了他们鉴定许久却得不到答案的几个标本,而吴征镒却用流利的英文说出了每一种植物的拉丁学名及其科、属、种、地理分布、资源开发的意义等。英国人佩服得五体投地,说“植物电脑”所称不虚。在日本札幌,吴征镒还未走进城边的小树林,便对同行的日本科学家说这里必然会生长的植物,令他们大为吃惊……
“植物电脑”“活字典”这些雅号在熟悉他的人看来,是必然。
武素功老师年轻时经常与吴征镒一起去野外调查。“他这个人,从来不知道疲倦,爱做笔记,走到哪儿做到哪儿,很少和别人聊天。我们去西藏考察回来后,有机会去青岛疗养。走的时候,他带了一皮箱书。我们俩住一屋,他中午从不休息,就坐在桌前整理从西藏带回来的标本。累了,他就趴在桌上打个盹。疗养一个月,他竟然整理出了一本《西藏植物名录》。”武素功说。
“他是植物地理分类学最伟大的践行者。即使很多地方没去过,他也能准确地说出该区系的植物。”弟子孙航对老师很敬佩。孙航在做雅鲁藏布江植物科考时,曾在那里找到一棵松果,并带了回来。他找到吴征镒,说这是一棵高山松。可吴征镒却很肯定地告诉他绝对不是,这棵要么是新种,要么是南亚的松。事实证明,吴征镒是对的。
“为学无他,争千秋勿争一日。”这是吴征镒送给学生的一句教诲,也是他一生淡泊名利、严谨治学的写照。
2007年,吴征镒91岁。他应任继愈先生之邀,担任《中华大典·生物典》的主编。此时,吴征镒的眼疾已经很严重了,家人反对他参与这项繁重的工作。但是吴征镒说:“我不做,谁来做?”为了编出让自己和世人满意的书,他倾其全力,开始重读清代的《草木典》。2007年,吴征镒只能看清3号加粗大字,医生对他说一定不能过度用眼。可他却回答:“我再不看,就没时间了。”吴征镒仍天天据案疾书。到了2009年,吴征镒的眼睛再也看不见了。吴征镒便让助手念给他听,再据此鉴定整理。一直到2012年3月,他因身体不适再度入院,也从未停止过手头的工作。
“为人学,学为人;先立志,后献身。”吴征镒用他的行动,表达了他对科研无悔的执着。92岁时,吴征镒获得了200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在同行研究者眼中,吴征镒胸襟广博,勇于担当,是个真正的大家,是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山。他无私地亮出自己的研究成果,无论是对国外同行还是国内同行;他倾心教授学生,没有一私保留。在朋友和家人眼中,他宽厚大度、深沉隽永,也是一座山。他情感丰富,爱父母家人,爱植物世界,也爱平凡生活;他唱昆曲、摄影、收贝壳、吹笛子、写格律诗。在世人眼中,他是一座永远让人充满敬意的高山,镌刻着执着和奉献。青山,无悔!
来源:《云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