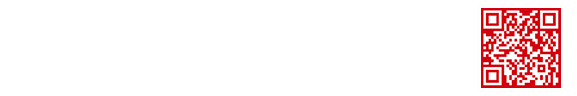◆李 娟
清明时节,梨花又开放。记忆中,家乡的三棵梨树在春风里鲜活如初。一棵梨树在青萝河的麦田边,一棵梨树在外婆的小院里,一棵梨树在我们家的红薯窖边。春天里,一树树洁白的花朵绽放在田野间和农家小院里,清丽脱俗,淡雅芬芳。每到梨花盛开时,就会想起奶奶和外婆,想起童年里那些温暖的往事。梨树下,那个仰着脸看花飘落的女孩儿,时隔多年后,双鬓已经生了白发。那白是童年里的梨花白。
小时候,奶奶清明节前去给老外婆上坟时,也会带着我。祖孙俩走在春天的山路上,我一会儿看看路边的紫花地丁和蒲公英,一会儿看看山坡上黄色的刺玫,走到小河边时,还会捡几颗小石子,打几个水漂,走着走着,就到了中午。到青萝河时,奶奶直接带着我去坟地里,奶奶边烧纸钱边哭。看着奶奶哭,我哇哇大哭,也不知道哭的什么意思,就是不能看见奶奶流眼泪。奶奶见我号啕大哭,又哄起我来。奶奶说:“三三,看,多好看的花儿啊。”顺着奶奶手指的方向,我看到麦田不远处一棵开花的大树,粗粗壮壮的,枝枝杈杈遮盖了一大块地方。奶奶告诉我,这棵梨树已经有很长的树龄了,秋天时会结满小小的梨,果子很瓷实,味道酸酸的,很少有人采摘。我只被满树雪白的花儿所吸引。花瓣随风飘落,落在我们的头上、衣服上和手掌心里。我在原地打着转儿,感觉自己就是春天里的花姑娘。秋天,再次去上坟时,我特意摘了几个果子尝了尝,的确如奶奶所说,果子并不甘甜多汁,果核很大,果肉很少,口感酸涩。但是,我在心里已经记住了这棵梨树开花时最美的样子。
外婆家的院子里有一棵梨树,因为是酥梨,每年春天的花朵又白又大又拥挤。春天时,一树的花染白了整个小院儿;秋天时,结的果子黄澄澄,酥脆、甘甜。外婆的孩子们多,但她总不忘给我留几个酥梨。如今,故乡不在了,梨树早已化为乌有,外婆也离开多年。然而,每年梨花盛开时,我都会想起在梨树下笑着迎我的,那个肤色白皙、瘦瘦小小、干干净净的外婆,想起童年里的宠爱和呵护,想起热腾腾的鸡蛋面,想起“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无奈和悲哀。听奶奶说,外婆年轻时是我们那里最好看的姑娘,虽然长在山区,但是皮肤特白,两条乌黑的长辫子,双眼皮大眼睛,身材娇小,柔柔弱弱。但是,一场场变故,经历了很多心碎的场景,这个瘦小的女子依然一步步走过来。外婆得了糖尿病之后,身体每况愈下,更加瘦小。父亲和母亲一起带着外婆求医问药,根据医嘱合理搭配饮食,悉心照料外婆。后来,因为父亲得了一场大病,母亲在北京照顾。有一次,我去看望外婆时,看到外婆原本白皙的脸上脏兮兮的,就用毛巾擦了擦,原来是好多天没有洗脸的缘故,那时候,她已经瘦弱得只能躺在床上。我边给她洗漱,边掉眼泪。外婆离世时,我守护在身边,祈愿在另外一个世界不要有疾病、伤痛,永远春暖花开。外婆如梨花一样永远洁白、清秀。
我们家的院子里有两棵树,一棵雪梨树,一棵石榴树,还有一片西番莲,大朵大朵的红色花瓣,一层一层,比向日葵还像笑脸。树和花给山区小院增添了雅致,也给孩子们带来了很多乐趣。雪梨是父亲从外地带回来的一棵梨树苗,栽在红薯窖边上。父亲说,这棵梨树耐寒,果实到冬天才完全成熟。我们就盼啊盼,看它开了一茬茬的花儿,终于长出了果实。母亲禁止我们去摸果子,原因是会落果。冬天,雪梨终于成熟了,有几个生了虫子,但是多数是完美的样子。和酥梨不一样的是,雪梨的颜色是褐色的,但是味道极甜、果肉细腻。母亲采摘下来,给我们留几个,把其他的分给了亲戚和邻居。山区当时还没有压面机,我们吃的炒面,都是母亲手擀的面条,面条细而劲道,上笼蒸熟,和豆角、鸡蛋一起炒,焦黄、奇香。炒面做成后,母亲会先盛一碗,让我给奶奶送去。当时,家里但凡做了好吃的,母亲总会让我们先给奶奶送去,比如做了饺子,蒸了包子,烙了油饼。后来,奶奶和外婆相继离世,对于村子里的长辈们,每个春节,她都会带着礼品上门看望。母亲对长辈的尊敬是从眼里到心里。她的一言一行影响着我们,我们也影响着自己的孩子,相信我们的孩子也会影响着他们自己的孩子,一代又一代。母亲,是我心里永远的雪梨,不问寒暖,只管开花结果,把最好的留给别人。
梨花,是心之所向的花。在故乡被黄河水淹没之后,每个春天,我都会去找梨花、赏梨花、拍梨花;《梨花又开放》是我听了无数遍的歌曲,童声让我想起童年,想起梨花一样的故人。我愿是岁月长河里一棵开花的树,那树是梨树,那花是梨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