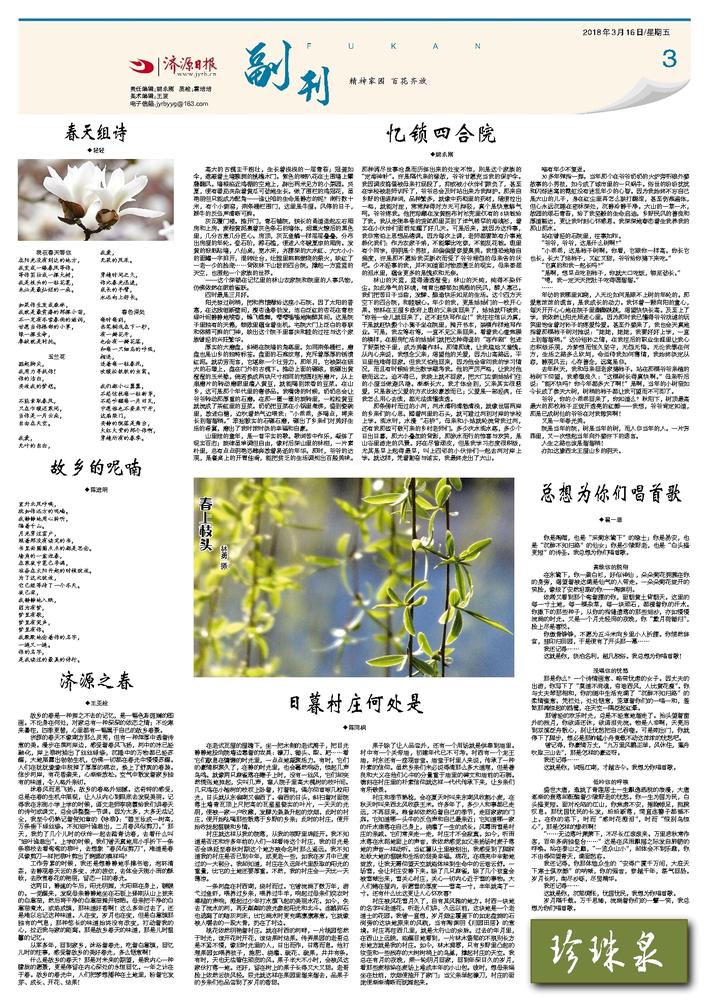◆陈同枫
在老式瓦屋的屋檐下,坐一把木制的老式椅子,把目光静静地投向院墙边靠着的农具:镰刀、锄头、犁、耙……看它们歇息在慵懒的时光里,一点点地凝聚活力。有时,它们的豪情积聚久了,在静的时光里,也会蓦然响动,惊起几声鸟鸣。就像两只麻雀落在鞭子上时,没有一丝风,它们却突然慌张地掠起,尖叫几声,窜入院子里高大槐树的枝叶间。几只鸡在小榆树的枝杈上卧着,打着盹,偶尔仰首啄几粒阳光,日头就从东偏南又偏西了。偏西的日头,斜扫着对面院落土墙青瓦顶上尺把高的瓦星星瓷实的叶片,一天天的光阴,便被一家一户收藏,发酵为袅袅升起的炊烟。此时的村庄,便开始吆喝那些散落于乡野的乡亲;此时的村庄,便开始收拢起温暖和乡情。
村庄就这样从我的院落,从我的视野里绵延开。我不知道是否还和许多年前的人们一样看待这个村庄,我的目光是否会绵延至春秋时期这个地方被命名时那么遥远。我不知道我的村庄是否已到中年,或更老一些,如我在岁月中已度过的一大部分。我却知道,村庄在久远年代里汲取的阳光的重量,比它的土地还要厚重。不然,我的村庄会一天比一天薄凉。
一条河盘在村西南,绕村而过。它曾流淌了数万年,游弋过鱼虾,喂养过乡亲,喂养过牛羊,响起过母亲们浣衣时棒槌的声响,溅起过少年打水漂飞起的美丽水花。如今,失去了流水的河,再无粼粼的波光参起阳光和北斗。连鹅卵石也逃离了的暗灰河床,比它淌水时更充满凛凛寒意。它就像被人嚼去的一段大骨,扔在了村边。
桃花依然明艳着村庄。就在村西的河畔,一片桃园悠然于时光,该开花时开花,该结果时结果。侍弄果园的老哥总是不紧不慢,像旧时光里的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打理果园如喂养孩子,施肥、浇灌、疏花、疏果,井井有条。有时,天也无法管住顽皮的风。果子半大不小时,会被风这家伙打落一地。还好,留在树上的果子长得又大又甜。老哥脸上依然云淡风轻。辰光就这样在果园里溜来溜去,品果子的乡亲们也品尝到了岁月的香甜。
果子除了让人品尝外,还有一个用场就是供奉到庙里。村中有一个关帝庙,初建年代已不可考。村西有一个龙王庙,村东还有一座观音堂。庙堂于村里人来说,传承了一种朴素的信仰。虽然乡亲们未必说得清那么多大道理,但是善良和大义在他们心中的分量重于庙里的碑文和庙前的石狮。镌刻在村庄里的朴素信仰就这样一代代传承下来,让乡亲们有所敬畏。
村庄和季节熟稔,会在夏天时叫来东南风收割小麦,在秋天时叫来西北风收获玉米。许多年了,多少人和事都已走远,不再回来。粮食却依然沿着自己的季节,走回家家的门扉。它知道哪一头牛的反刍声和自己最亲近;它知道哪一家的汗水滴落在自己身上,浇灌了一生的成长。风霜雨雪是村庄的亲戚。它们常来走一走,村庄才不会寂寞。如今,听雨水落在水泥地面上的声音,我依然感觉如父亲扬场时麦子落地的声音一样动听。当红薯从土里被刨出,我感受到了脚踩松软大地的温暖和生活的甜美幸福。棉花,在棉壳中辛勤地绽放,让我无需仰望天空就能体味到生命中的云卷云舒。一场雪,会让村庄安静下来。除了几只麻雀,除了几个孩童会被雪喊出来,雪关心村庄,关心一切内心近于雪的事物。大人们蜷在屋内,祈愿雪的厚度——雪高一寸,丰年就高了一寸。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心怀欢喜?
村庄被风花雪月久了,自有其风雅的地方。村西一块地的名字叫老道花。听老人们讲,久远以前,这块地是一个老道士的花园。我曾一直想,岁月烟尘覆盖下的如龙盘旋的石岗旁的这块地原来的风貌,当有陶渊明《归园田居》的意境。村庄再往西几里,就是太行山的余脉。过去的年月里,在西山上远眺,能醒目地看到,一片林木蓊郁的不规则长方形地方就是我的村庄。如今,林木凋零,只有乡野里凸起的坟茔和一些残存的大树树梢上的鸟巢,撑起村庄的天空。我总在有月的夜晚,乘一轮明月回家,回到年深日久的岁月,看那些麦秸垛在麦场上堆成丰年的小山包。彼时,想母亲端坐在灶前,炊烟便推开了家门;当父亲举起镰刀,村庄的面庞便渐渐清晰而妩媚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