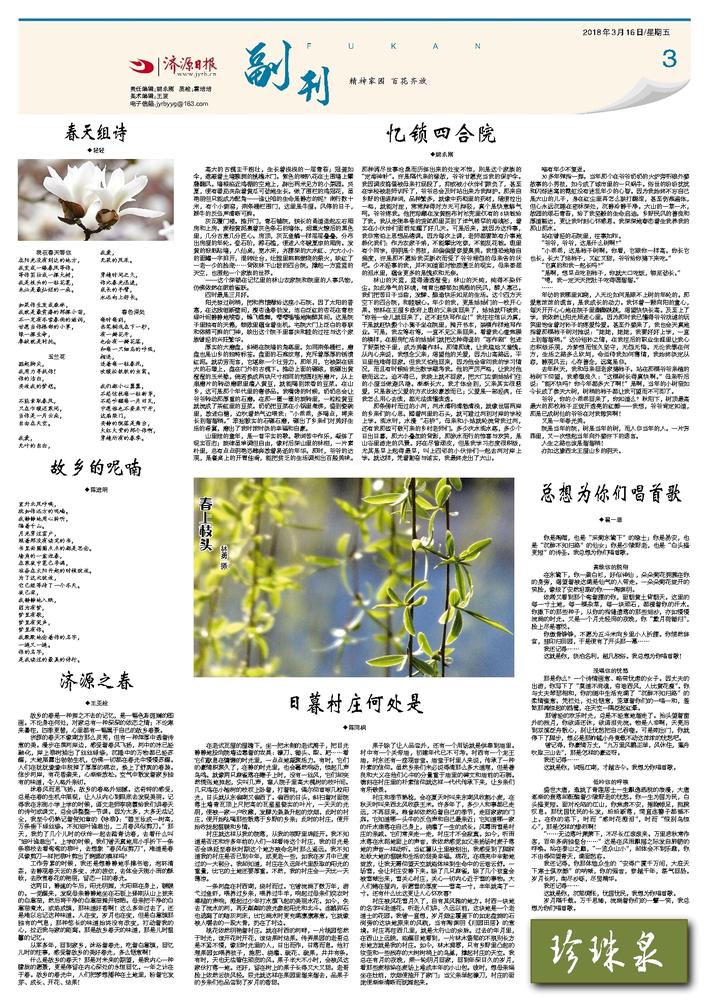◆姚永刚
高大的古槐主干粗壮,生长着浅浅的一层青苔;冠盖如伞,遮蔽着土墙簇拥的挑檐木门。紫色的喇叭花在土围墙上攀藤翻风。墙根临近鸡棚的空地上,辟出两米见方的小菜园。炎夏,便有番茄夹杂着黄瓜可劲地生长。做了围栏的鸡冠花,虽艳丽但只能成为配角——谁让咱的生命是静态的呢?南行数十米,有个小侧窑,荆条栅栏围门,这里是牛屋。风停的日子,耕牛的反刍声清晰可辨。
灰瓦覆门楼。推开门,青石铺院,狭长的甬道连起左右厢房和上房。麦秸黄泥裹着灰色条石的墙体,烟熏火燎后的黑色里,几分古意几分匠心。房顶,灰瓦鱼鳞一样层层叠叠,分布出房屋的年轮。登石阶,跨石槛,便进入冬暖夏凉的厢房。发黄的报纸贴墙,八仙桌,宽木床,齐腰深的大水缸、大大小小的面罐一字排开,混砖灶台,灶膛里熊熊燃烧的柴火,映红了一老一少的脸庞……背依林下山坡的四合院,撑起一方蓝蓝的天空,也围起一个家族的世界。
——这个深锁在记忆里的林山农家院和院里的人事风物,仿佛依然在眼前雀跃。
四时最是三月好。
阳光掠过树梢,把和煦馈赠给这座小石院。因了太阳的普惠,在这残垣断壁间,瘦杏逢春勃发,洁白泛红的杏花在青枝绿叶间静静地喷香,蜂飞蝶舞,嘤嘤嗡嗡地陶醉其间。这是院子里独有的天籁,颓败里蕴含着生机。宅院大门上泛白的春联和依稀可辨的门神,映出这个院子里喜庆和睦的过往与这个家族曾经的兴旺繁华。
厚实的大磨盘,斜倚在院墙的角落里。如同荆条栅栏,磨盘也是山乡的独特标签。盘面的石痕纹理,充斥着厚厚的锈渍红泥。就功劳而言,它堪称一个壮劳力。那年月,它被架在硕大的石墩上,盘在门外的古槐下。推动上面的碾磙,能碾出黄澄澄的玉米糁。倘若换成两块尺寸相同的短圆柱形磨片,从上扇磨片的转动磨眼里灌入黄豆,就能喝到浓香的豆浆。在山乡,这可是那个年代里的奢侈品。我嘴馋的时候,奶奶总会让爷爷转动那厚重的石磨。在那一圈一圈的旋转里,一粒粒黄豆就流成了茶缸里的豆浆。奶奶把豆浆在小锅里煮沸,盛到瓷碗里,放进白糖,边吹着热气边喂我:“小乖乖,多喝点,将来长到溜溜梢。”笨拙敦实的石碾石磨,碾出了乡亲们对美好生活的希冀,磨出了我时浓时淡的幸福和自豪。
山里娃的童年,是一首平实的歌。歌词苦中作乐,凝练了现实百态;旋律虽单调但自由,像村后深山里的林相,一片素朴里,总有点点明艳恣肆奔放着易逝的年华。那时,爷爷的达观,是餐桌上的开胃佳肴,能把贫乏的生活调剂出百般美味。那种阅尽世事沧桑而历练出来的处变不惊,则是这个家族的“定海神针”。许是隔代亲的缘故,爷爷甘愿充当我的保护伞。我因调皮捣蛋被母亲打屁股了,抑或被小伙伴们欺负了,甚至在学校被老师训斥了,爷爷总会及时站出来为我辩护。那来自乡野的俚语辩词,品种繁多,就像中药柜里的药材,随便拉出一格,就能对症,常常辩得对方无可辩驳,真个是快意解气呵。爷爷疼我。他把珍藏在发黄粗布衬衫兜里仅有的6块钱给了我。我从走街串巷的货郎那里买到了洋气稀罕的海魂衫,着实在小伙伴们面前炫耀了好几天。可是后来,就因为这件事,我非常怕上思想品德课。因为每次上课,老师都要煞有介事地教化我们:作为农家子弟,不能攀比吃穿,不能乱花钱。班里有个同学,明明是个男孩,却偏偏爱穿爱臭美。我惶恐地暗自揣度,许是那不愿给我买新衣而受了爷爷埋怨的母亲告的状吧。少不经事的我,并不知道面对物质匮乏的现实,母亲委屈的泪水里,蕴含更多的是愧疚和无奈。
林山的天蓝,蓝得通透澄莹;林山的天纯,纯得不染纤尘。如此净气的环境,哺育出醇郁如美酒的民风,醉人惠己。我们把苦日子当曲,发酵、酿造快乐知足的生活。这个四方天空下的四合院,和睦暖心。年少的我,更是姑姑们的一枚开心果。预料在王屋乡政府上班的父亲该回来了,姑姑就吓唬我:“你爸一会儿就回来了,还不赶快写作业!”我往往信以为真,于是就赶快搬个小凳子坐在院里,摊开书本,装模作样地写作业。可是,我左等右等,一直不见父亲回来。看着我心虚焦躁的模样,在厨房忙活的姑姑们就把这种得逞的“恶作剧”包进了野菜饺子里,成为美餐作料。那情那境,让我尴尬又羞愧。从内心来说,我想念父亲,渴望他的关爱,因为山高路远,平日里他难得回家。但我又怕他回来,因为他会审问我的学习情况,而且有时候给我出数学题考我。他的严厉严格,让我对他敬而远之。迫不得已,我晚上就不回家,把大门左侧姑姑们住的小屋当做避风港。渐渐长大,我才体会到,父亲其实很慈爱,只是表达父爱的方式比较豪放而已;父爱是一部经典,任我怎么用心去读,都无法读懂读透。
那条傍村而过的小河,河水清冽清澈清浅,就像世居两岸的乡亲们的心思。踏着河里的石头,就可蹚过河到对岸的学校上学。涨水时,水漫“石桥”,母亲和小姑就轮流背我过河,还有我那些可敬可亲的乡村老师们。多少次水涨水落,多少个日出日暮,那大小叠加的背影,那涉水而行的惊喜与欢笑,是山谷里游走的风景。好在尽管顽皮,但是我学习态度很积极,尤其是早上起得最早,叫上四邻的小伙伴们一起去河对岸上学。就这样,凭着勤奋与诚实,我最终走出了大山。
唯有年少不复返。
30多年弹指一挥。当年那个在爷爷奶奶的火炉旁听狼外婆故事的小男孩,如今成了城市里的一只蜗牛。俗世的纷纷扰扰和闪烁迷离的霓虹没有迷乱年少的心智。因为我始终不忘自己是大山的儿子,身在红尘里再怎么跌打翻滚,甚至伤痕遍体,但心永远沉睡在密林深处,沉静冷静干净。大山的一草一木,故园的顽石青苔,给了我坚毅的生命启迪。乡野民风的善良和厚道豁达,更让我时刻心怀感恩。我深深地眷恋着生我养我的那山那水。
站在曾经的石院里,往事如昨。
“爷爷,爷爷,这是什么树啊?”
“小乖乖,这是柿子树啊。你看,它跟你一样高。你长它也长,长大了结柿子,又红又甜,爷爷给你摘下来吃。”
“它真的和我一起长吗?”
“是啊,想早点吃到柿子,你就大口吃饭,铆足劲长。”
“嗯,我一定天天把肚子吃得圆溜溜。”
……
年幼的我哪里知晓,人无论如何是跟不上树的年轮的。那爱意浓浓的谎言,是我成长的动力。我怀着一颗向阳的童心,每天开开心心地在院子里蹦蹦跳跳,渴望快快长高。及至上了学,我依然让阳光照进心里。因为那时我已懂得爷爷戏谑的玩笑里饱含着对孙子的疼爱怜爱。甚至外婆来了,我也会天真地指着那棵柿子树对她说:“姥姥,姥姥,我要好好上学,一直上到溜溜梢。”这份祖孙之情,在我往后的职业生涯里让我心态积极乐观,为梦想而恒久坚守,无怨无悔。无论我漂在何方,生活之路多么坎坷,命运待我如何薄情,我始终淡定从容,静观风云;心存善念,远离是非。
去年秋天,我和母亲回老家摘柿子。站在那棵爷爷亲植的柿树下仰望,我感慨良久:“这棵树长得真快啊。”母亲听后说:“能不快吗?你今年都多大了啊!”是啊,当年的小树苗如今长成了参天大树,树梢的柿子都让我可望而不可即了。
爷爷,你的小乖乖回来了,你知道么?秋阳下,树顶最高最大的那枚柿子正绽开透亮的红颜——我想,爷爷肯定知道,那是已成树仙的爷爷在对我微笑啊!
又是一年春光美。
院是当年的院,树是当年的树,而人非当年的人。一片芳菲里,又一次想起当年向外婆许下的诺言。
人生之路也该是溜溜梢!
亦如这豫西北王屋山乡的明天。